|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
|
2010年2月18日 0:41:02
|
收藏本站 | 设为首页 |

|
|
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中的中国学术精神
连心达
美国丹尼森大学
关键词:对文学经验的高强度直接感知;有机整体观;传统中国学术精神
内容提要:宁稼雨倡导创建的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在两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亦即对经验的高强度直接感知和对大结构大关系的有机整体把握。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因子纽结”,故事主题类型为旨在揭示民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材料新角度,开启了新可能。
宁稼雨教授所倡导创建的“中体西用”叙事文化学之所以能在“西用”上卓有成效,是因其能克服长期以来在“师夷长技”上存在的盲目性与无自主性,而其于此领域之理论与实践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指标性意义,尽在其对“中体”的清楚认识和坚持,以及对传统中国学术价值的成功回归。
一、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实践性——对文学经验的高强度直接感知
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已被公认为民间文学研究“不可或缺”[1.195页] 的“阿尔奈-汤普森AT分类体系”,虽然在以“泛欧洲”为主的民间故事研究工作上行之有效,但若要运用到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上来,其普适性无疑会有局限。大多数论者注意到了这个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可能产生的问题,但鲜少有人去注意这一分类体系本身的特殊性,辨析其合理与否。而宁稼雨的理论表述和实践接触到了这一方面问题。
如宁氏所言,中国叙事文化学应包含“两个互有关联的组成部分:第一,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第二,对各个故事主题类型进行个案梳理和研究。”[2.36] 此处的第一方面,其实就是通过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特别倚重的“AT分类法”来编制自己的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的想法。宁的理论表述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与西方主题学研究微妙的区别,强调了对研究对象的分类和对故事类型的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有关联的”。在另一处论述中,这个意思有更明确的表达:“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的工作,其一为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其二为故事主题类型个案研究,其三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三者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索引编制是基础,个案研究是主体,理论研究是指南。”[3.19] 此处多了“理论研究”作为指南一项,统领全局,用意不言自明,而索引编制与个案研究的关系,前者是工具是基础,后者是主体是目的,后者要重于前者,说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宁氏主题学与西方主题学的指导思想和目的之差异,已经见出。
以东方之“己”度西方之“人”,我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索引就应该是个工具,其实不然。为索引而索引的事例,一如为艺术而艺术,在西方传统中比比皆是。虽然AT分类体系建立之后,已经“引”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那是后“索”者追出来的“无心柳”,而非先“引”者“有意”的初衷。索引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其与作为索引后续工作的研究是可以割裂开来的。或曰,这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初衷的指导思想会左右,甚至决定索引的性质。在其1955年版《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的序言中,汤普森就宣称,其六卷本皇皇巨著“并不企图确定叙事艺术中各种母题的心理基础或它们的结构价值,因为尽管这些因素有其价值,但我认为这种价值对于民间故事和神话的系统整理没有多少实际帮助。”[4.10] 生怕读者不解其意,汤普森把这意思毫不含糊地再强调了一次,“虽然这样一个巨细无遗的清单[索引]可能已经为某种哲学讨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此索引本身却有意回避这种讨论。”[4.11] 此处所谓“哲学问题”是广义的,大概是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美学之类,或任何其它高大上论题。很明显,他要的东西非常简单,即纯粹的系统整理,巨细无遗的清单。
系统的整理,琐细的面面俱到的清单,这就是个问题。阿尔奈-汤普森AT分类系统列出了2499个故事类型,分列在一个由5个大类,19个小类,小类下又有次小类、再次小类组成的叠床架屋的数字系统之中。上面提到的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是有别于AT故事分类的一个母题分类体系,将23500个故事母题分列于23种类,每个种类之下有大类,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下有次小类,次小类之下还可再分。大类以下的项目以基本整齐的十进制架构组织排列。不可否认,这两个相互配合的,条理清楚秩序井然的分类系统,虽也隐含着项与项、类与类、项与类之间在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上的相似、重叠、对照,和远近、亲疏等复杂关系,因而可以呈现故事类型或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发生、分布、流传与变异情况,但这种呈现的最终目的还是在明“类”之分别,以求对各个类的单一特性做更精确的定位(因此这种民间故事研究可以为社会群体身份辨别提供某种文化标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分类系统所力求的尽可能整齐的格式和尽可能完备的容量。比如,为了维持其完整全面的十进制排列架构,汤普森的母题索引编号系统还留出了不少尚无任何实际内容,必须等待将来新发现来填充的“空号”。这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性”的向往,可以用汤普森自己的话来解释:“如果试图将世界上所有传统叙事材料浓缩为秩序(像科学家在处理世界性生物学现象时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单个母题——即构成完整的叙述的分子——进行分类。”[4.10] 西方文化传统中强调形下现象背后的形上理式的思维惯性,对纷繁具象背后的抽象的、因而是纯粹而绝对的“真理”的执意追求,表露无遗。简言之,西方主题学的分类系统体现了一种通过对现象世界的认定来达到对“规律/真理”的掌握的思想文化潜意识。
与此相比较,以“中体”为原则的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在材料的处理上大异其趣。如前所述,中国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从一开始就给主题类型的分类索引工作定了调,即分类必须为个案研究服务。“正确梳理和描述分析个案故事的文化意蕴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灵魂和要义。”[3.20] 唯其如此,类如何分,索引如何编制,都要以是否能为主题类型个案的文化文学解读分析提供充分的“前提条件”为标准。在这里,看不到那种对全面的,秩序井然的,能够与生物学分类相颉颃的类型索引系统的渴望,而只有对具体类型赖以建立的主题之具体内容的“合适度”与“充分度”的要求。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虽然目前已经有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切入点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的索引编制工作,但从总体上说,研究者的着力点大多落在叙事文学史上的某些明显的“富矿”地带。我们看到的是对一个个具体故事类型中的丰富的关联重叠关系的关注,而非对某种大而全的“中国版AT分类系统”的急迫盼望。可以设想,即使将来某一天有一个接近完整的中国叙事主题类型索引库终于在集体的努力下产生,研究者们大概也不会因其库存材料之全之有条理之科学而感到终极的满足,而只会因研究工作的素材有了保证而觉得心中踏实。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完备的类型索引库还没最后形成的时候,宁氏就已经在考虑如何从资料库中遴选适合进行个案分析研究的故事类型,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遴选标准和操作方法。这种在材料的搜集分类过程中就引入对类型分析的深思熟虑,让二者从一开始就互为因果的做法,在过度重视纯粹的“系统整理”和“巨细无遗的清单”的阿尔奈-汤普森西方思维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这便是中国叙事主题研究“以中为体”的精神所在。不同于对事物背后的抽象秩序的求索,对生动的事实的直接的高强度的感知和参与才是类型研究的目的。认知的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前面提到的西方主题类型分类系统极力回避的对“哲学问题”的讨论,不正是宁氏所提倡的“中体”主题类型研究的最终关切么?
研究目的不同,其搜集材料的目光所及,也必定有异。AT分类系统想要囊括的,是所有的故事类型或故事母题,而中国故事主题类型研究要寻找的,是可作为文化文学分析的主题类型。这个“主题类型”究竟为何物,必须弄清楚,否则便会出现“对‘主题’、母题’、‘原型’、‘类型’等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各持其说,莫衷一是的现象”。[5] 针对这一问题,宁氏提出了“单元故事”的概念:“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目标既不是母题情节类型,也不是完整的一部作品,而是具体的单元故事。”[6]“单元故事”是一个重要发明,具高度实用价值,可作为中国主题类型研究中一个专门术语固定下来,功莫大焉!
西方主题学类型研究中的基本单位是作为类别的故事类型或母题。“故事类型”(tale type)的基础是情节,其含义不难理解。作为类别,其所强调的是“类”中各分子的同质。“母题”(motif)的情况则较复杂,各家说法不尽相同,简单地说就是在故事中重复出现的,具有能引发联想的特殊含义的最小“故事意义”单位。作为类别,其强调的是“类”之主旨的重复。无论是“故事类型”还是“母题”,二者的存在意义均在其“类”之独立,无论其与它类之关系如何,都是对其作为有别于他者的“类”之身份的肯定。譬如,尽人皆知的《灰姑娘》(AT分类510A)和《白雪公主》(AT分类709)分别为两种不同的故事类型,但其中都出现了恶毒后母(母题索引S31)这一母题。《灰姑娘》中有“水晶鞋”(母题H36.1)和“逃离舞会”(母题R221)这两个《白雪公主》中没有的母题,而《白雪公主》中的“魔镜”(母题D1163)和“被毒苹果毒死”(母题S111.4)这两个母题亦为《灰姑娘》所无。
宁氏提出的“单元故事”虽也叫做“类型”,但此“类”非彼“类”,更是种模式或模型(mode),其在意的是同一个模式中所有参加者的同中有异,异中有意的色彩纷呈的面貌,以及这种多样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拿宁称之为“以中为体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范本和楷模”[6.100] 的研究对象孟姜女故事来说,其单元故事很单纯,就是“妻哭夫”。在这个单元故事模式里,包含了无数个具体的“妻哭夫故事”的多样变体。其情节各异,可以“不受郊吊”,可以“哭之哀”,可以“崩城”,可以“畅其胸中”。具体追查下去,连“崩城”这一具体情节因素也有自己的演进过程,所“崩”之“城”从无名到有名,从虽有名而并不实指到实指的“长城”之“城”。故事的主角则前有《左传》之杞梁妻,后有梁武帝《河中之水》之莫愁女,当中还插了个托身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中的无名氏“贱妾”,一直到北宋才正名为“孟姜”。而追根寻底,却发现《诗经》里早有美女,其名“孟姜”! [7]
如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AT分类系统要的是“分”:强调个体类型之外的相互关系(相同、相似、差异等),而以单元故事为基本单位的中国故事主题类型学想的是“合”:重视个体类型之内各个分子之间的关联。前者通过总结加概念化的方式企图将故事提炼为公式或标尺,为西方民间故事类型的“客观”界定设立标准;后者通过联系比照组合来扩大单个故事所包含的经验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前者要剔刻出骨架,后者要丰满以血肉。一个是干净纯粹的单一,一个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组合体。虽皆名“类型”,其旨趣大不相同。
当然这是极而言之的粗线条概括,具体地局部地看,AT分类系统也有与“合”相关的因素,如故事类型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发生、流传、变异等情况的比照,然而这种“合”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分”的明确。中国主题类型学在面对该分的情况时也毫不犹豫地分,如《六朝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就因材料制宜,分出天地、怪异、人物、器物、动物、事件六大类。但这种分不是为分而分,或为主观想定的“目录学”架构而分,而是为了发现主题类型的聚合点,为更有效的“合”造出坚实的平台。
从类型编制的结果上看,AT分类系统为一内涵与外延都相当清晰的概括性种类的全部的完整有序的排列;而宁氏的类型设想则是数目不定形状各异不规则地散布在不同平面不同处所的多层次存在。一追求种类的全面、规整和秩序,呈现了“客观”事实/知识;一欣赏具体的多样和丰富,再现了时空维度上活生生的经验。打个比方,AT分类系统就像一个巨大的标本室,纲目清楚层次分明地展示着2499种鱼“类”之代表,准确地标示着其产地,存在生态等与鱼有关的事实。而中国故事主题类型学呈现的则是数目不定的,外形参差不齐的,散布在不同平面的上大大小小的“单元放生池”,每个池中活动着种属相同或相近的但个体形态有异的鱼群。这是有心的渔人从五湖四海有目的有选择“竭泽而渔”来的收获,是同属一个单元的所有“鱼”个体的聚集地。
两个系统,孰是孰“更是”,可以慢慢体会。
西方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出于西方用于西方,固然有其自适性与合理性。但其对形而下现象背后之抽象理式的期待与痴迷的独特西方性,却不容否认。前面提到的汤普森的母题索引清单居然可以为尚未发现的母题预留空格的做法, 便反映了对形而上规律的信心,不禁让人想起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故事。中国文化思想传统中没有这种基因,“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并不是夫子不解形而上学。面对谜一般的时空之“逝”,孔子亦有动于中,然圣人不尚“空”谈,最终还是可触可感的“川”的流动,才让“逝者如斯夫”的感慨,感性地落到人心实处。正如一位深谙中西世界观差异的汉学家所言,中国人没有形而上学那一套,不认那种所谓能统摄宇宙一切的绝对秩序。从偏重理性的西方世界观的角度看,其也有所失:他们没有由抽象的理式而推导出的事物之可知性和可预测性的概念。然而其也有所得:他们对事物运动变化的奇妙有某种高强度的直接的感知、参与和体会。[8.54]
宁稼雨倡导并苦心经营的叙事主题类型研究的“中体”特性,究其实,就是这种对现象世界的全身心感知和参与的求实在精神。其根本特点是对问题的整体把握。从总体规划层面看,材料的搜集分类过程也就是类之模型慢慢生长成型,分析工作的目的方向愈加清晰,基本论点逐渐形成的过程。从操作层面看,为了确定一个故事类型能否能真正成为个案研究有分量的研究对象,宁稼雨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入选标准,即文本流传的时间跨度、文本流传的体裁覆盖面和类型的文化意蕴。在具体操作中,特别留心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强调综合、关联和流动,避免拆分、片面和固定。硬性条件在某些情况下当属必要,而综合考虑权衡却是更高的原则。[3.19–21] 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在强调整体关系。
二、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有机整体观——对大结构大关系的系统把握
正是这种有机整体感,使得主题类型研究可以突破和超越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的界限,把因为文体不同而各自独立的文本视为一个系列整体。再回头细看“孟姜鱼”,一个单元故事类型,有几千年的时间跨度,有精神实质相近而表现形式不同的多层次文化意蕴,更重要的是,它有历史有哲学有诗歌。正因其有着跨学科跨体裁的生动存在,所以若想摸清与此单元有关的全部情况,便不得不跨越。这不是选择,是必然。而被跨越的,不只是个体故事之间,更是体裁之间,甚而至于学科之间一条条人为的分界线。
谓其“人为”,只因其自然本无。这就牵涉到了一个讨论中国叙事主题类型学研究时不能不较真的问题。或许并非巧合,那篇把孟姜女单元故事之来龙去脉辨析得一清二楚的力作的作者是顾颉刚,学贯文史哲的史学与民俗学大家、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符号,而其出现的时间,1924年,正是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在中国攻城掠地,进而“登堂入室”,反客为主的年代。顾颉刚以其对传统中国学术融会贯通精神的坚持,为“中体”学术传统在一个世纪后的重新调整振作埋下了一个结结实实的伏笔。
说到此处,笔者要扯一段闲话,90年前,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José Ortegay Gasset 1883–1955) 给狭窄的专门家下了个定义:“他并不博学,因为他对任何不进入其专业领域的事物都一无所知; 可他也非无知,因为他是个‘科学家’,对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那个小角落了如指掌。我们只好说,他是一个渊博的无知者。”[9.112] 2007年,当深陷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对正与之缠斗的敌手“失去感觉”之时,著名战略学者和地缘政治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敏锐地感觉到了一种认识论危机:西方思维自以为可以用数学般的精准来对待历史人文信息之模糊与复杂,习惯于从巨大的丰富之中抽取出干净利落的原则、公式和数据,从而将纷繁的时空现实有条不紊地安置于专门化学科分门别类的硬性框架中。而今,在面对一个非西方的陌生对手的时候,这种惯常的自信突然感到无力。专门但碎片化的“科学”测量规定和“客观”却专断的分解剖析钝化了人们对事物整体的感知,眼前的世界突然测不准了。专门家可以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多方面把伊拉克局势分析得头头是道,却看不清路边炸弹从何而来,因何而来。感慨之下,卡普兰想起了加塞特当年的言说,他告诫人们,不要再任由狭窄的专门化“科学”思维把自己变成一个“渊博的无知者”了。[10.80]
是伊拉克战争的残酷现实让卡普兰认识到了专门化认知方法的缺陷。其实,在此之前,从上世纪末开始,当中国知识界的先觉者们一步步认识到自五四运动以来全盘西化文化思潮对传统文化造成的严重伤害之后,就把审视的目光投向在文学研究领域占领了至少半壁江山的西方学术范式的负面影响。正是这一契机触发的反思运动,促使当时已经意识到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所处窘境的学者开始检讨文体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这种专门化研究方法对叙事文学研究的制约掣肘。因缺少西方“呐喊者”的坦率与极端,中国的谦谦君子们没有使用“渊博的无知者”的说法,但他们对带碎片化倾向的专门化研究方法之认识的痛切,必定更甚于加塞特与卡普兰。原因无他: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问的是“何种认识论偏差让我们选择了那条‘专门细化’歧途?”追查的是自家遗传病的根源;而中国人要反省的,不是“为何误入歧途?”而是“为何舍弃自己的正路,而选择他人之歧途?”
“渊博的无知者”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见木不见林”。对于这种思维方式上的近视病,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生的免疫力。凡事先见林,并倾向于将一切“木”作为“林”来处理,似乎是古汉家人的看家本领。文史哲不分家,也是开天辟地以来一直如此的故事。再看语言,一定是宇宙观里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才让中国人选择了具有独一无二的“观念整合性”的汉字。[11.58] 汉字系统究竟为何物,表音?表意?还是表其他?为什么至今没有确切答案,是不是正因为本来就没有答案,而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伪问题?庄子有言:“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也就是说,假使一“物”没有形体,没有体积,没有重量,你怎能测出或表述它的“精粗”轻重?譬如,有可能说水多么粗糙,土多么透明,或光多么重吗?汉字系统不是“音”、“意”或什么其他计量单位可以衡量把握的。因其不仅仅是“语言”,所以无法用围绕“语言”转的概念来定义它。现下“再汉字化”论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语言观具有‘世界观’的本体论的意义,古代语文学家必定循着人对自然、人文世界观察与理解的逻辑顺序与轨迹去把握汉语的语法规律。”[12.312] 此说十分精辟,似已窥见到汉字系统的本质。不过,用我们所理解的“语言”这一概念——即使已经将其无限提高到了世界观和本体论的高度——还是不足以穷汉字系统的实质意义。
笔者忽发奇想:是不是可以说汉字系统其实是华夏人为了构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互观照的“虚拟现实”而发明的一个系统?它不记录现实,而是直比现实。这样一个广大融通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编码”(找不到更确切的词)系统可以被“分”,被“围”,被“粗细”这样的概念来专门化地规定吗?《马氏文通》之前,词只有虚实,并无“词类”一说,一按西人之法分类,问题就来了。虽说有了条分理析的方便,可遇上“春风又绿江南岸”,便不知所措。本来王荆公只是想在汉字的虚拟世界中对一个生命现象作尽可能接近的把握,并不知道有“形容词作动词用”这回事。“绿”并非只是一个词,是个生命现实。而“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中的颜色,究竟是“动词”还是“形容词”?根本说不清楚,其实,为什么只提动词形容词?这五彩缤纷之中说不定还有什么“动”与“形容”之外,无法被“分”被“围”,因而至今尚无法被归类的什么属性。
一旦问题可作如是观,那么,中国叙事不容专门化研究随意碎片化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古人之叙事,不只是叙述记录,而是企图在一个“虚拟现实”中回味、揣摩、体验、体会、想象、再(创)造,在此意义上,叙事与史异曲同工。史之所以可“鉴”,就因其并非简单机械的记录,而是个与“实”同时存在的虚拟实在“镜像”。西方学者看中国史觉得像小说,看小说又觉得像史,大惑不解。他们不知道对中国古人来说这并不是个问题。古人不去计较什么是最高真实。只要对现实有整体的把握,便无须担心事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被模糊。跟汉字系统一样,中国叙事不是在事实背后追赶的一种表述工具,而是一个直指事实直比生活的“虚拟现实”。假如对其“混沌”状态不满足,企图将其门类化,又是体裁分别,又是断代区隔;又是作家的特殊,又是作品的单一,“日凿一窍”,结果必定是“七日而混沌死”。
事实死于“凿”的暴力,而凿者还自以为得计,沾沾自喜。我们今天在“社会科学”的一些部门看到的许多怪现象,便属此类。结果是,琐细的表象昭昭,整体的实质昏昏。门类科系的分类并非事物本来的属性,而是人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强加给事物的规定,即使这种规定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能通过实验手段检验的“硬科学”)符合“客观”事实,也绝对不可能是事实的全部。“在学术界,专业化在成为必需品的同时,也成了诅咒。一方面,有太多的狭隘的专业知识已走到了智慧的对立面,而另一方面,爆炸性增长的信息材料又要求人们在每一个知识领域进行更为狭隘的细分。”[10.80]于是,才有卡普兰呼吁我们抛弃无知的狭隘型“渊博”,回归事实——通过“原初的情感”(raw emotions),[10.80] 亦即没有被“科学”专门化加工、污染、歪曲的对事物本真本初的整体直觉。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宁稼雨要大力提倡在研究工作中突破和超越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的界限,并将这一做法视为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最大特点。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中国主题类型个案研究的实践,就可以看出,其所致力的,并不只是机械地突破和超越文体之间和作品之间的“物理”界限,而是要突破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理念与范式影响之下形成的某些因人们习惯成自然而视而不见的成规,超越所有妨碍我们将研究对象视为有机整体的一切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近视性做法和封闭式思维。其目的只有一个,要恢复被专门化、门类化教条割裂破坏了的,被机械简单的封闭式思维模糊了的事物中原初的有机联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举个例子,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例子。
在谈到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中必然会遇到的材料取舍问题时,宁氏指出:
……任何个案故事的材料本身都具有文化实践和文化认识的价值。它本身是否存在,是个案故事的文化发生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化信号。有些材料尽管只是承袭或是用典,但这承袭和用典本身就是文化发生过程的符号。如同孔子的言论,有的时代整体受宠,有的时代整体遭贬,有的时代部分言论受宠,有的时代部分言论遭贬。决定和制约这其中背后的力量恰恰就是每个时代价值好恶观念的体现。而这宠贬的历史就是文化自身内涵的发展历史。[13]
是故,在主题类型材料的选取上,即使是“基本上沿袭前人的文字或者只是作为典故出现的诗文”也“不能放弃”,因为“这些承袭或用典的个案故事材料也是其整体故事文化链条中的有机部分,剔除它们则意味着个案故事材料文化链条的断裂”。[13]
我们可以接着用前面的比喻来看这问题,西方故事分类系统问的是“何种”鱼,注重的是“类”,而中国叙事主题研究之“竭泽而渔”却企图将与一类型“单元鱼”有关的一切信息一网打尽,即便是两条个体的鱼看起来一摸一样,也要收入网中,因其不只在意鱼之“类”,而更关心每一条具体生动的鱼“因何”而出,活动于“何时”、“何地”,“如何”自处,与其他鱼又“有何”互动。
由此可见,宁氏以上这一番言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材料取舍(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的范围。因其考虑到如何“从潜在文化因子的角度来系统观照和整合历史文化”,[13] 便点到了主题类型个案研究(第二个层面)的实质内容,而以主题类型研究为着力点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研究(第三个层面)的大用和意义,亦已不言自明。
宁氏的论述,让人想到了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提出的一个理论:
一件新作品问世之日,也就是此前所有作品同时受到触动之时。经典作品本已构成一个自在的理想的体系,一旦有新(真正新)作品进入,现存体系就得进行相应的调整。若还想在新事物进入之后继续生存,原本已经完备的整个体系就都必须随之改动,即使这种改动可能是细微的。这样,每一个作品与体系整体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以及由此而呈现的价值都得到调整,新与旧因此得以相互适应。[14.5]
艾略特这段话的实质,与宁稼雨的观点若合符节。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一如其对“旧”的偏爱与强调,在文化问题上多持保守立场的艾略特对“新”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怀疑。新事物倘不是“真正新”,便不入其法眼。而对宁而言,与原生主题有关的任何后出材料都有新意,不可轻易放过。即便是“沿袭”与“用典”,也不会只是对主题的简单重复,而必然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新经验与再演绎。尽管其给现有体系带来的“改动”可能是“细微”的,但毕竟也是改动,体系中的每一个分子“和体系整体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以及由此而呈现的价值”都因这种改动而“得到调整”。
如此看来,宁氏念兹在兹的“主题类型”,其实就是艾略特所说的“传统”,因为每一个故事主题类型个案都是由或旧或新或大或小或重或轻的多个作品组成的一个即使不完全“理想”,亦已自足自适的,在新分子加入之前就已相对完整的体系,同时又是一个因为有新事物的参与而不断生长变化不断自我调整的活的有机整体。要之,每一个故事主题类型,都是一个小传统。
三、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开启了诸多新可能
如果以上关于传统的有机整体性的说法言之成理,那么,只认识到每一个主题类型都是一个小传统还不够,因为,从更高的视点看,每一个小传统又在另一个层次上成为一个更大的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因子”。换言之,没有哪个主题类型个案可以独立存在,而总要被纳入一个传统关系网。这是否就意味着,以单位故事为核心的主题类型研究在叙事学研究的其他方面,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格局中可以起到,也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在这里笔者想通过对一个或几个个案的还不成熟的思考来谈谈对这一设想的看法。
正好是一百年前,眼见国人在“铁屋”中酣睡不醒,面临着“从昏睡入死灭”而不自知的巨大危险,鲁迅奋起“呐喊”,喊出来的第一声就是《狂人日记》。这部作品如今尽人皆知,但在当年,却很有可能无人理会,这是因为,能将中国四千年文明总结为“吃人”的,其狂也无疑,而狂人的话是不会被当真的。狂人越是企图证明自己正常,在正常人眼里他的就越不正常。如果价值判断只能在一个维度里进行,那么狂人永远摆脱不了这个两难困境。于是鲁迅在狂人的日记文本之外,造出另一个文本,另一个维度:即带出日记的引言。
这引言其实得当“后记”看:日记中的所有狂乱在这里都得到了理性的解释。读者被告知,“救救孩子”并不是故事的最终结局,狂人在病愈之后不但幡然悔悟,把自己病中日记定性为“狂人”文字,而且如今已“赴某地候补矣”,将要成为其曾痛批的“吃人”机器上的一个部件。经历了日记中的谵妄躁动之后再回头读引言,顿觉一切都平静下来。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异迫使读者在感情和理智上做一个判断选择:一为引言之“正常人”世界,一为日记正文之“不正常人”世界,哪一个“正常”?
鲁迅没有告诉读者如何选择,因为作者的强力介入只会跟狂人的自证和呼吁一样苍白,但他使了个引导手段:读者反复比照体会之下,会发现“正常”世界使用的原来是文言,与日常话语距离甚远。而“不正常”狂人的大白话,“错杂无伦次”的“荒唐之言”却与自己每日生活不可或缺的言谈息息相关。当年的读者最后如何抉择,如今已无探究的必要,百年后翻天覆地的中国已经告诉我们,虽然日记中的狂人失败了,历史上的狂人鲁迅却获得了成功。
这故事似曾相识?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结构让我们想到了另一段千古奇文: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
原本也就一庄周,却生出“栩栩然胡蝶”和“蘧蘧然周”的两相。蝴蝶梦中隐含的二元对立结构让我们警觉起来,这不是狂人的问题么?不同的只是,一旦打破“一受其成形”带来的“我”的迷思,庄子忽然一身轻,可以声称不知自身究竟是周还是蝶。狂人却无法享受哲学家才有的奢侈,“梦”(病)中是栩栩然的狂人,“醒”(痊愈)后却须蘧蘧然觉悟,刻意用言语否定自己曾经的不正常,并以实际行动证明现的已经完全正常。他只能要么被人叫做狂人,要么被自己叫做狂人。旧制度的顽与“痼”在鲁迅笔下得到最充分的揭露,效果极其震撼。
这效果是不是得益于蝴蝶梦,鲁迅写作时是否真的想到庄子,在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解读亦不能置一喙的“作者已死”文学批评后现代已无多大意义。我们可以指出的是,《狂人日记》引言中“荒唐之言”一词确为庄子所造,鲁迅沿用的也是庄子的原意(而非此词现时的贬“意”):“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天下》)。
不禁由此联想到,拒绝与时代之浑浊合流的狂人母题在《庄子》中多次出现,最典型的有“楚狂接舆”。当然,在庄子之前的《论语·微子》中就有“狂接舆歌而过孔子”的记载。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称“陆通,字接舆,楚人也。”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和成玄英《庄子疏》皆循此说。楚狂或可能确有其人,若是,假以顾颉刚先生的学识与耐力,我们说不定还能挖出些跟接舆有关的故事。一个“狂人”主题类型,呼之欲出?
于是我们把大网撒开,又忽然有发现,《列子•周穆王》一篇,也有个狂人:“秦人逄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视白以为黑”与正常人比,其价值观完全倒错,症状与鲁迅笔下狂人无异。听说“鲁之君子”能治他儿子的病,逄氏便“之鲁”,路遇老聃。老聃听其告诉之后说,谁说你儿子病了?“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觉者。……天下尽迷,孰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如汝子,汝则反迷矣!”是天下人都病了,反诬没病的少数为狂人。这形势与《狂人日记》几乎完全一致。
有趣的是,老聃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连我自己都不知自己有没昏病!这口气听起来很熟悉,原来是庄子的话。《齐物论》中,就在“蝴蝶梦”出现之前,庄子感慨到,天下人都在大梦中而不自知,都自以为“觉”。为了自证其说,庄子又大大方方承认“予谓女梦亦梦也。”我说你们都在做梦,其实说这话时,我庄子自己也在梦中,我的判断亦为梦话。而一说到梦,就不能不再提到蝴蝶梦!
问题开始变得复杂且有意思起来。令人浮想联翩。从鲁迅《狂人》之二元对立立刻想到蝴蝶梦,立刻想到楚狂接舆,立刻想到《列子》中的狂人,又因列子言语中泄漏的信息立刻回溯到了庄子,反证蝴蝶梦与狂人的微妙联系。中国人——尤其是对中国“文史哲”有所浸染的中国人——的想象在这 一层都应该是能够如此跃进的。
当然,必须指出,蝴蝶梦的二元对立结构并非为狂人而设,庄子关心的是认识论的问题。假如醒觉的庄周不比梦中的蝴蝶更真切,那么实与虚也就无差别了。[16.59] 但以此“正-反”结构来考察正常与不正常,或狂与觉的关系,不能再合适了。亦即是说,虽然“蝴蝶”与“狂人”明显分属不同主题类型,但若从审美问意的角度看,这两个类型之间某些方面的实质意义关系却有可能比各自营垒中同类因子之间的同类关系还重要。“狂人”的说服力不能不借助于“蝴蝶”,而“蝴蝶”的意义又可因“狂人”的佐证而更显深厚。
然而故事还没说完,“蝴蝶”之后,还有“黄粱”。作为“蝴蝶梦”的主题类型远(近?)亲,“黄粱梦”在寓言象征意义上与其高度近似。此梦源远流长,家喻户晓,在此无需赘言。但可以指出的是,无论是《黄粱》是《邯郸》是《南柯》甚至《烂柯》,无论是志怪是传奇是话本是元杂剧、或是日本古代现代小说和能剧的《黄粱》变体,均属狭义的故事主题类型之第一层次。待到曹雪芹将其活用在《红楼梦》的“引言”(比之于《狂人》引言?),即第一回女娲补天之类“荒唐之言”之后(作者自况“满纸荒唐言”,庄子所造“荒唐”一词在《红楼》第一回出现了三次,在结尾两次,不可不留意),“黄粱梦”单位故事顿时获得了更高一层的意义。太虚幻境入口处大牌坊上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但有《黄粱梦》之现世体验得出的认识,更有《蝴蝶梦》于认识论高度上的大彻大悟,甚至,作为文学理论,尤其是叙事学理论,也十分贴切。这两个不同的梦,好像有割不断的联系。
纵览“全局”,似乎还是鲁迅对一切“梦”的深刻认识与真正消化,才有《狂人日记》中对梦结构的不留斧凿之痕的最巧妙运用。如果说《红楼梦》的“引言”(还得加上全书结尾处对引言的呼应)是《黄粱梦》之3.0版的话(在《黄粱》与《红楼》之间还有《牡丹亭》之类的2.0),那么,《狂人日记》结构框架的神来之笔便是“蝴蝶梦”4.0无疑。其体现的已经不是文学类型,而是思维方式。
以上这一通联想,实起于单元故事,但又不囿于单元故事。以单元故事为基础的主题类型研究实实在在地为包括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在内的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户,提供了一个新领域。在此新领域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往前看,是不是还可以更有野心?如前所述,从更高的视点看,每一个主题类型小传统又在另一个层次上成为一个更大的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主题类型研究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们从整体看问题,从大结构上理关系。一个类型个案自身内部的情况弄清楚之后,似可再往前一步,留心此个案与他个案的关系,进而看出个案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因子在整个叙事学研究中,以至于在整个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与意义。
由于围绕着单元故事的所有同类型因子在内容上的高度重叠与近似,在表现形式特点方面却有互相关联的多样与不同,而同一类型中所有因素又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上纵横交错地进行有机的团结与纠缠,故类型中的每一个作品都是这个三维网状结构上的一个纽结,互为原因结果。这些个“竭”五湖四海而得来的大大小小的强力集成构造所产生和聚集的多层次多维度新鲜意义,不可能自我消化在各自封闭的“类型躯壳”之中,而必定要从各个方向往外溢出放射。这种外向意义放射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相互的,由此产生的结构性意义交集又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一个更宽广的三维网状意义系统。许多原本不容易被发现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能启发新思维的作品中有意义的细节,有可能在对主题类型这种文化因子纽结的观察中被揭示出来。以单元故事为出发点的研究方法为文学文化多方面研究工作的进一深入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新可能。诸如民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审美习惯、思维方式等等,都可以成为主题类型研究的关注热点。诚如前引宁稼雨所言,主题类型研究应有“从潜在文化因子的角度来系统观照和整合历史文化”的抱负。[13] 而既然“类型”也是一种“模式”,期望通过对主题类型的整体性研究来揭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民族思维特性的想法,或许也不为过。
与历史一样,文学文化史也充满了诡异。上面提到的艾略特那篇保守意识浓重,但又是以新锐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对传统的真知灼见发表于1917年。一年之后,文化革命激进派鲁迅却以《狂人》的一声呐喊将中国之一切传统作为一盆脏水不加区别地全数泼出。诡异的是,正是这篇反传统的文字,最生动地体现了艾略特与传统有关的又一言简意赅的论断: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必须“不仅活在此刻的当下,而且也活在过去的(一个个具体的)当下”;(就整个文学传统而言)他所感知和意识到的“不是已死的东西,而是早就活生生地存在过的东西”。[14.11] 痛恨传统的鲁迅应该最懂传统,否则便不会有对“蝴蝶梦”的创造性活用,或在《故事新编》中演绎的深刻与机智。能用自己的创作来生动体现中国古老传统中的“现代性”,却看不出,或拒绝看出中国传统中的精华,这种因爱恨交加而产生的悖论,令人感慨万千。
令人感概的还更在于,宁稼雨所致力的中国叙事主题类型研究,正是对百年前鲁迅等一批救亡图存心切的知识精英在向西方学习问题上某些急病乱投医的做法的反思和纠正。1607年,《几何原本》书成,尽管其内容是“纯”数学,与意识形态无涉,译者徐光启也意识到这一刻对中国学术的一统天下意味着什么,“其私心自谓:不意古学废绝二千年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其禆益当世,定复不小”(《刻<几何原本>序》)。以徐氏之聪明,当不至于将欧氏几何学与“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混为一谈,然西学虽好,中体的权威不可动摇,其维护传统之苦心孤诣,令人动容。而此中西交流项目的背后推手利玛窦,也极其小心,顺着中译者的意思,将欧几里得打扮成华夏“百家”之一:“是书也,以当百家之用,庶几有羲、和、般、墨其人乎”(《刻<几何原本>序》)。可见“中体”的坚持是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即使是中华传统中最不抱残守阙者李贽,对利玛窦敬佩有加,称其“是一极标致人也”,“我所见人未有其比”,也不能不问,一个外国人“到中国十万余里”,“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与友人书》),对西学的进入充满高度警惕。不料,几百年后,当西学放下一切顾忌,到中土侵门踏户之时,知识界不但没有李贽的一问再问,不知到此何为?不知到此何干?反将自家之所有自行扫地出门。痛定思痛,今天“中体西用”学术思想的出现反映了当代学人对中国学术乃至中国文化之前途的忧虑、思考和关怀,其所表现出的凛然气概与深刻见识,令人敬佩。与当年的鲁迅们一样,当代知识分子亦以天下为己任,但与痛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先贤不同的是,在中华民族已经有史为鉴,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今天,21世纪的中国学人可以较为从容地认清道路,思考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学术话语权的问题。
走笔至此,得解释本文题目中的“鱼之乐”了。“竭泽而渔”的收获,是故事主题类型研究者的“渔之乐”,而此乐之来源是丰富生动的,不容为门类碎片化研究破坏的中国叙事文学中的原生态“鱼之乐”。中国“文史哲”史上有这么一段寓意深长的对话: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
庄子是否偷换了“安知”这一词的概念来作诡辩并不重要,其最后之大不耐烦的要害,在于对惠子机械的碎片化的研究态度的否定和批判:你的三段论逻辑是谁规定的?别人的学术范式我为什么就得遵守?我的“鱼之乐”之知,来自整体经验,来自濠中之“游”的对经验的高强度直接感知之实在和真切。
参考文献
[1]艾伦·顿迪斯(Alan Dundes). "The Motif-Index and the Tale Type Index: A Critique"(评母题索引与故事类型索引)[J].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民间故事研究), 1997, (3):195–202.
[2]宁稼雨. 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体西用”范式重建[J]. 南开学报,2016, (4):32–37.
[3]宁稼雨. 关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入选标准与把握原则——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丛谈之六[J]. 天中学刊,2015, (4):19–21.
[4]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A Classific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in Folktales, Ballads, Myths, Fables, Mediaeval Romances, Exempla, Fabliaux, Jest-Books and Local Legends, 6 vols. (《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民间故事、民谣、神话、寓言、中世纪罗曼史、劝喻故事、小故事诗、笑话及地方传说之叙事因素分类》6 卷本).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5(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1卷.
[5]郭英德. 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理依据[J]. 天中学刊,2012, (3).
[6]宁稼雨. 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97–103.
[7]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J].歌谣,1924, (69).
[8]安乐哲(Roger Ames)为其Sun-Tzu: The Art of Warfare: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Incorporat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Yin-ch’üe-shan Texts (《孙子兵法;包括新近发现的银雀山竹简之首个英译本》)所写的长篇导言.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3(纽约:Ballantine 出版社,1993年版),3–99.
[9]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 (José Ortegay Gasset 1883–1955).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大众的反叛》)[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55(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55年).
[10]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 “A Historian for Our Time”(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历史学家)[J]. 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 ),2007,(1、2月合刊):78–84.
[11]申小龙、孟华. 汉字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再汉字化[J]. 西部学刊,2014,(2):57–60.
[12]申小龙.语言文字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3]宁稼雨. 对《关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若干思考——以“高祖还乡”叙事演化为例》的回应意见[J]. 天中学刊,2017,(1).
[14]T. S. 艾略特 (T. S. Eliot).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传统与个人才能)[C]. 见Selected Essays(《艾略特文选》).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4 (纽约:Harcourt, Brace & World出版公司,1964年),3–11.
[15]连心达. “Redreaming the Butterfly Dream”(再梦蝴蝶)[J].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现代中文文学 ),1999,(1):103–129.
[16]葛瑞汉(A. C. Graham). The Book of Lie-tzu: A Classic of Tao (《列子》英译).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
“That’s What the Fish Enjoy”: Towards A Themat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nda Lian
Denison University
Keywords: intense awareness of the immediacy of literary experience; holistic grasp of phenomena; Chinese scholarship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nopsis: An intense awareness of the immediacy of literary experience and a holistic grasp of the object of its investigation are the two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thematology” advocated by Ning Jiayu, which focuses on the modes of story. As the study of the modes is in a sense the exploration of “nexuses of cultural elements,”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llective psychology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tendencies in aesthetic judgment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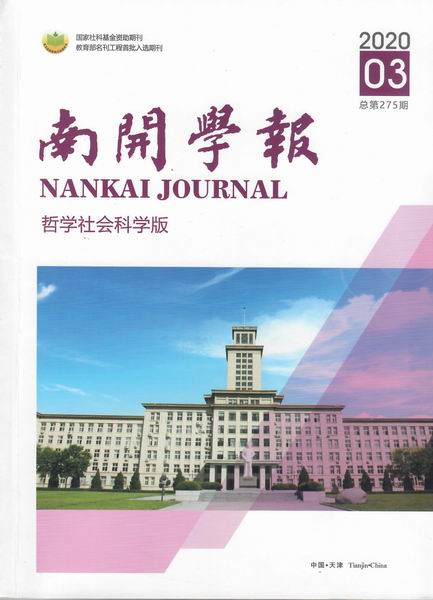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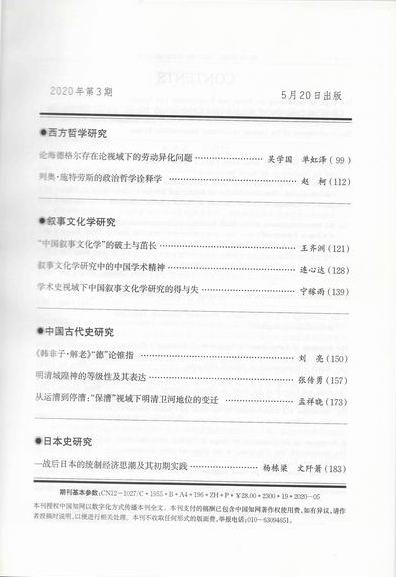
(本文原载《南开学报》2020年第三期)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