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破土与茁长
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文学理论批评与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宁稼雨教授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新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小说研究者的学术本位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一理论尚需要更深入的论证,以确定其内涵与外延,还需要排除各种可能的误解,以减轻理论的阻力和压力。就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小说研究而言,20世纪的主要问题不是“作家作品研究”等研究范式的制约和影响的问题,而是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所带来的对中国古代小说门类的扭曲与伤害的问题。如果“中国叙事文化学”是要回归中国叙事文化之“体”,其所借用的“叙事学”、“主题学”等西方的理论只是研究这些本体之“用”,并且尽量容纳一切能够阐明中国叙事文化特质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那么,“中国叙事文化学”就能够茁壮成长,成为21世纪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成熟理论。
关键词:中国叙事文化学;叙事学;主题学;故事类型;小说观念;中体西用
新世纪以来,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提出了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并身体力行,发表了一批关于如何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以及应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叙事文学主题类型的论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些论著主要有:《主题学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天中学刊》2007年第1期),《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关于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什么要“以中为体,以西为用”?》(《天中学刊》2012年第4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重建》(《天中学刊》2013年第4期),《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作用》(《天中学刊》2013年第6期),《重建“中体西用”中国体系学术研究范式——从木斋的古诗研究和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说起》(《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6期),《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联与特质》(《天中学刊》2014年第3期),《“中体西用”:关于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的思考》(《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体西用”范式重建》(《南开学报》2016年第4期),《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孙悟空叛逆性格的神话原型与文化解读》(《文艺研究》2008年第10期),《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移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4期)等。我虽然一直关注着稼雨教授的研究,却没有参与有关的讨论,主要是自己还没有看清楚,想明白。最近,抽时间系统阅读了有关著述,有了一点心得,故提出来请稼雨教授和学术界的朋友们指教。
一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是新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小说研究者的学术本位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值得充分肯定。而这一要求由稼雨教授提出,则是天时、地利、人和作用的结果。
先说“天时”。
“中国叙事文化学”吸收了叙事学、主题学、文化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成果,而这些学科成果主要源自上世纪80年代涌进中国的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这些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经过绍介、理解、消化、吸收,被中国学术界接受下来并加以应用,一直延续至今,成果相当可观。而有些在当时更为风靡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如“新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则似乎没有这么幸运,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某种理论和思潮的起伏沉浮,其中原因也许很多,但最为根本的,恐怕还是与这种理论和思潮是否切合中国学术实际、是否能够产生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直接相关。就叙事学而言,尽管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学者托多罗夫(T.Todorov)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中正式提出,但作为“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在西方却是长期存在的。而在中国学术界接受这一理论,将它运用于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中国民间故事和通俗小说的研究后,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单篇论文这里不计,仅在90年代出版的与叙事学相关的著作就有罗纲《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庆信《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书社,1995年)、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彬《红楼梦叙事》(工人出版社,1998年)、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等。
主题学研究也是如此。主题学被认为是从19世纪德国民俗学热中培养出来的一门学问,德国人原来称为“题材史”,法国人称之为“主题学”,美国学者则将其定义为“打破时空的界限来处理共同的主题”的一种研究范式。主题学很早就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工具。在民俗学里,“主题”常被称为“母题”或“故事类型”。在神话学里,又被称为“原型”。芬兰民俗学者安蒂·阿尔奈(Antti Aarne)创制、美国民俗学者斯蒂思·汤普森(Stith Thompson)改进的AT分类法,是一套划分童话类型的分类方法,在学术界影响深远。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便被视为西方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理论基础。而德裔美国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发表于1937年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归纳出中国故事的306个类型(其中正格故事类型275个,滑稽故事类型31个)。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1978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则将7000多个中国故事归纳为843个类型。这些研究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国内 ,促进了中国叙事文学尤其是民间故事的研究。台湾学者得风气之先,所获成果也较大陆为早,中国文化大学的金荣华教授是其代表,他于1984年出版的《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索引》是国内最早关于小说主题索引的著作,只是他将“故事类型”改换成了“情节单元”。有些没有以主题学命名却实际上受主题学影响的研究著作也还不少,如敝校著名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刘守华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著作。他在该书《绪论》中说:
本书的研究方法上所作的探索就是:在尽可能占有丰富故事材料的基础上,从母题、类型入手,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解析比较、综合,力求准确而深入理解故事的实质及其附着人类文化流程的“生活史”。书中选取了近20个著名故事类型用上述方法进行评述。如列入唐代的《〈田章〉和天鹅处女型故事》这一节,从被称为“天鹅处女”或“羽衣仙女”型故事的众多异文中抽取出四个最有代表性的亚型,构成历时性序列,构拟出它的“家谱”,再对包括《毛衣女》、《田章》、《天牛郎配夫妻》、《召树屯》、《诺桑王子》等许多脍炙人口之作的相关文本特色与价值进行评说。这样来审视民间故事,就有别于一般文学史的写法,而能够从微观到宏观、从静态到动态,较好地揭示出作为口头语言艺术主要样式的民间故事的特殊本质了。
从刘著中可以看出,作者非常自觉地运用主题学(“母题”、“故事类型”)做民间故事的历时性研究,写成了中国第一部民间故事史。钟敬文先生认为“作为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一本著作,它已经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作者的一些追求及其所采用的学术路径,是可以在稼雨教授的理论追求和学术路径中发现端倪的。
稼雨教授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正是在近几十年中国的有关研究的学术积累,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学术积累的基础上,顺应学术发展内在要求而提出的,所谓“瓜熟蒂落”,此之谓“天时”。正如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提出“叙事学”并非向壁虚构一样,稼雨教授提倡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也非凭空设想,而是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发展到新世纪新时代而自然发生的学术文化要求,就如埋在地下的种子遇到适合的气候条件,如水分、阳光、温度、湿度等,就要发芽破土而冲出地面一样。
“中国叙事文化学”在新世纪初之所以能够破土而出,也得益于“地利”与“人和”。所谓“地利”,稼雨教授所在的南开大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镇,尤其是在文言小说研究方面积累深厚,他自己在1996年就出版了国内最早的一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1996年),后来又对《世说新语》进行了精细的耕耘,加上天津地近京畿,有许多便利条件,这些地利条件能够使他得风气之先,提出富有建设性的主张。所谓“人和”,则是稼雨教授与小说研究界的学者们沟通频繁,有良好的人脉关系,大家愿意参与意见,促进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健康成长。这只要看看稼雨教授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提出后,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积极响应,就足以证明“人和”的重要了。
二
一种理论的提出固然重要,但它能否经受住理性的拷问和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发展壮大,以致成为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成熟理论,需要走的路会很长,付出的心血一定会比提出这一理论所付出的心血更多。正好比一棵破土而出的树苗,要想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除了需要充足的阳光雨露和必需的土壤肥力外,还需要经受风吹雨打,抵抗烈日严寒,与周围的植物一起生存竞争,创造适合自身成长的内生条件和外在环境。如果不能这样,它就很难长大成材。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提出已经十多年了,稼雨教授一直在进行着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他的立义其实是很高远的。他将王国维和鲁迅开创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要点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体裁研究,二是作家作品研究。”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经典研究论著(《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和《中国小说史略》)本身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核心特质就是全面把西方文化背景下学术的体系移入中国”,“从这个范式形成和内涵性质来看,毫无疑问,它是‘全盘西化’文化背景对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制约掣肘的结果”。然而,“随着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就逐渐暴露出它于中国叙事文学本身的固有本质产生隔阂,因而有削足适履和隔靴搔痒的不足。它所忽略和难以解决的中国叙事文学比较集中和普遍的是跨越各种文体和跨越若干作家作品的故事类型研究”。因此,他“计划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做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其核心主线是围绕故事类型来构想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体系和范式。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集结方式,具有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属性和特点。它与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所关注的情节人物最大区别就是离开了单一情节和人物,去关注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正是这些情节和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变异轨迹,才能为整个该故事主题类型的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和素材”。所以,“从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故事类型研究既是对传统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补充和更新,更是对于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学术格局的颠覆和对于21世纪‘中体西用’学术格局的追求和探索”。
看得出来,稼雨教授是要用“中国叙事文化学”来“改革”20世纪传统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颠覆”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的学术旧格局,“追求和探索”并最终形成21世纪“中体西用”的学术新格局。这样宏伟的抱负是值得称赞的,它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担当。不过,从稼雨教授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描述中,其理论的自洽性似乎还不太够。读者的疑问是:“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一种学术理论还是一种研究范式?是一种学术策略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理论、范式、策略、方法并不截然分割,也非彼此对立,但侧重点毕竟有所不同。就学术理论来说,“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核心是什么?基本概念有哪些?它与西方叙事文化学(“文化主题学”)有何不同?如果没有,加上“中国”就没有意义。“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故事类型”或“故事主题类型”研究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为什么不用更通俗的中国故事类型研究?所有这些,都要有清楚明白的表述,要让人们真正理解“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真谛。
其实,“中国叙事文化学”不是不证自明的,它需要理论的论证,以确定其内涵与外延,还需要排除各种可能的误解,以减轻理论的阻力和压力。如果“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的叙事文化学”,其所关注和强调的就应该是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叙事文化”的“中国”特质。而“叙事文化”不仅包括叙事文学和其他叙事文体,而且也应该包括受叙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化类型和非叙事文体,如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因为只有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才能更全面更立体更准确更透彻地阐释中国“叙事文化”。如果“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叙事的文化学”,其所关注和强调的就应该是“中国叙事”所独具的“文化”特色。而“中国叙事”限定了其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叙事文学”和其他叙事文体,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和其他非叙事文体显然不在其观察和研究范围之内,其落脚点则是“中国叙事”的文化内涵及文化特色。张培锋教授曽撰文指出:“有关叙事文化学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论述的多是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而对于‘叙事文化’——即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却少有揭示。” 他还指出一些用典的抒情诗歌是不可以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注对象的。显然,培锋教授所理解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叙事的文化学”,抒情诗歌自然被排除在外。稼雨教授曽撰文回应,以为培锋教授误解了“中国叙事文化学”,他认为:“‘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它只能通过‘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去承载,去体现。在‘研究者选取的叙述故事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中,就已经包括了‘叙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身的内涵。’”。至于那些基本上沿袭前人的文字或者只是作为典故出现的诗文何以在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中不能放弃,理由之一是:“任何个案故事的材料本身都具有文化实践和文化认识的价值。它本身是否存在,是个案故事的文化发生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化信号。有些材料尽管只是承袭或是用典,但这承袭和用典本身就是文化发生过程的符号。” 很清楚,稼雨教授所谈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的叙事文化学”,一切非叙事文体,只要承载了叙事文化的因子或受其影响,便都可以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其实,两位教授所说都有道理,只是所指涉的概念并不一致,或者说对“中国叙事文化学”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这也说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还缺少自洽性,内涵还不甚清晰,逻辑也有欠严密,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此,“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茁长和成熟,还需要展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理论建设。
三
稼雨教授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是要“改革”20世纪王国维、鲁迅建立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旧范式,建立起21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新范式,要“颠覆”20世纪以来“西体中用”的学术旧格局,并最终形成21世纪“中体西用”的学术新格局。
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范式基本上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全盘西化’文化价值观作用下‘西体中用’文化价值观的产物”,这种判断我是赞成的。今日的学科分类以及学术理论、概念、范畴、方法,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经由日本)引进的,“郢书燕说”在所难免,其不能完全契合中国学术的历史实际是谁也不能否认也无法否认的。不过,在具体研究中,人们也不可能不从中国学术的具体实际出发,来落实这些引进的西方理论和方法,不然,这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就很难真正在中国学术界扎下根来,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在20世纪,不仅有王国维、鲁迅示范的“文学体裁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形成了影响最大的学术研究范式;而且还有以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歌谣周刊》第69号,1924年)为代表的一批故事主题类型研究著作 ,其学术成就也不容忽视,说其已经形成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自然也无不可。而无论哪种研究范式,它们虽然都受到了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但都照顾到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具体实际,故其学术成就也为学界所公认。我相信,这些能够照顾到中国叙事文学实际的学术研究范式,包括“文学体裁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是不会在21世纪退出学术舞台的,它们仍然会继续被研究者们所采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这样说,并非否认20世纪用西方理论建构中国学术所带来的对中国本位文化的扭曲和伤害。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扭曲和伤害主要不体现在具体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这些“用”的方面,而是体现在其学术思想、学科观念及其所形成的一整套学术体系这种“体”的方面。2015年底,我和张江教授就他所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有过一场学术对话,其间我谈到:
我们中国现在的一套文学体系基本上都是借用西方文论来谈中国文学,合乎西方文论的保留,不合乎西方文论的去掉,要么就是重新包装、重新整理塞进西方文论的框架中去。比如中国的小说,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及补志共著录小说1000多部,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小说只有几十部,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小说按西方小说概念来说根本对不上,所以不被承认。按西方观点,小说是要讲故事并且是虚构的。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从鲁迅先生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可我们要问,它是虚构的吗?刘义庆自称它是真实的,而且把裴启《语林》因为虚构而书不传作为鉴戒。再说志怪小说《搜神记》,记录鬼神,应该是虚构的吧,但当时人认为它是真实的,作者干宝本来是史学家,并被人称为“鬼之董狐”,董狐是春秋时著名的史官,人们认为他记录的东西真实可靠,所以《搜神记》长期被收录在史部,《隋志》、《旧唐志》都在史部著录。《晋书》是唐太宗亲自主持编撰的,《晋书》就把《搜神记》里的许多故事采写进人物传记里去,郭沫若就说《晋书》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这当然是今人的观念。所以说,我们用西方这一套理论解释中国古代文学时,出现不搭界的地方太多了。
在我看来,就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小说研究而言,20世纪的主要问题不是“作家作品研究”研究范式的制约和影响的问题,而是西方小说观念所带来的对中国古代小说门类的扭曲与伤害的问题。因为前者是“用”的问题,后者是“体”的问题。如果不明中国古代小说之“体”,如何能够证明我们是在研究“中国小说”,这样的研究如何可能具有中国特色?因此,稼雨教授提出要在21世纪用“中体西用”代替“西体中用”,我是十分赞成的。事实上,20世纪初期,对于究竟什么是小说,学术界是存在明显分歧的。1932年,郑振铎在撰写《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时曾说:“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乃是近十余年来的事。商务版的《小说丛考》和《小说考证》为最早的两部专著。但其中材料甚为凌杂。名为‘小说’,而所著录者乃大半为戏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才廓清了一切谬误的见解,为中国小说的研究打定了最稳固的基础。” 郑氏所说的虽然是当时的事实,但却并非科学客观的结论。因为他批评《小说丛考》和《小说考证》“凌杂”而肯定《中国小说史略》“廓清了”谬误的见解,只是站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立场上讲话,而不是站在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立场上讲话,其结论虽然符合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实需要,却并不符合中国文化本位的历史和逻辑。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与西方小说观念很不一样,故小说形态也斩然有别,钱静方的《小说丛考》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坚持的是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即视小说为“道听途说”、“稗官野史”;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采用的是由日本引进的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指认“有一定长度的虚构的故事”为小说。由于观念的差异,他们对研究对象的把握便很不一样。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就一定是一种错误的小说观念,而西方现代的小说观念才是正确的小说观念呢?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的先人所认可的小说并不是小说,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那些小说才能算是小说呢?如果是这样,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早已被后现代小说观念所打破,中国现时的小说观念正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那么,现代小说又应该以什么作为标准呢?2009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专栏,陆续推出了一批批“非虚构小说”,《光明日报》文艺版也发表过不少“非虚构小说”,此外,“网络小说”、“手机小说”正茁壮成长,大有赶超纸质文本小说的态势,小说观念的发展和文体的变异在所难免,我们凭什么说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是唯一正确的小说观念呢?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小说只能是“虚构的故事”而不能是别的东西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作为一定历史时段中国人对于小说的认识,中国史志和传统目录学著作所著录的小说是当时人所认可的小说,自有其文化依据和存在的价值,我们就没有理由否定它,只能客观地承认它,历史地理解它,科学地评价它。以此反观《中国小说史略》,它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构建的中国小说史的学术体系,是否真正尊重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实际?是否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待了各个历史时期真正发挥社会影响的小说家及其作品?是否真的理解了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实处境和实际作用?这些重大问题显然需要我们在21世纪理性对待并认真思考,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尤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不能回避的。当然,新世纪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对这些问题也是需要重视并予以解答的。
如果稼雨教授提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要回归中国叙事文化的本位,尊重既往的一切历史事实,他所提倡的“中体西用”的“中体”就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之“体”,他所借用的“叙事学”、“主题学”等西方的理论只是研究这些本体之“用”,在此基础上尽量容纳一切能够阐明中国叙事文化本体特质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包括“文学体裁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那么,“中国叙事文化学”就能够茁壮成长,成为21世纪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成熟理论。稼雨教授如有信心,我们就有理由予以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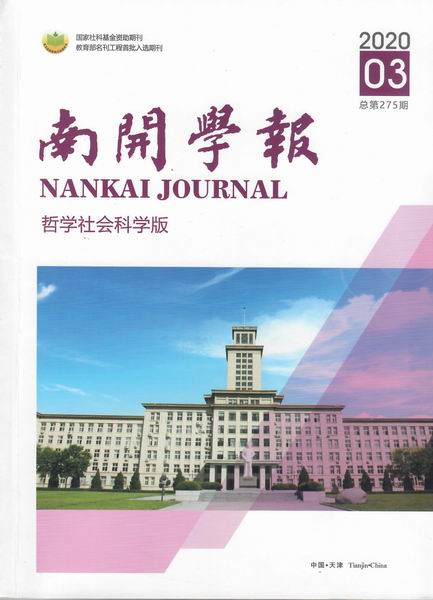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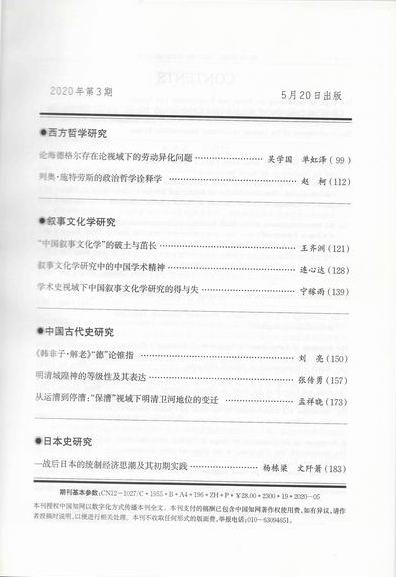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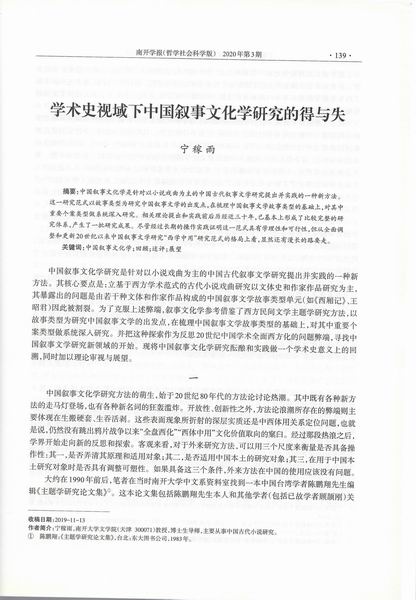
(本文原载《南开学报》2020年第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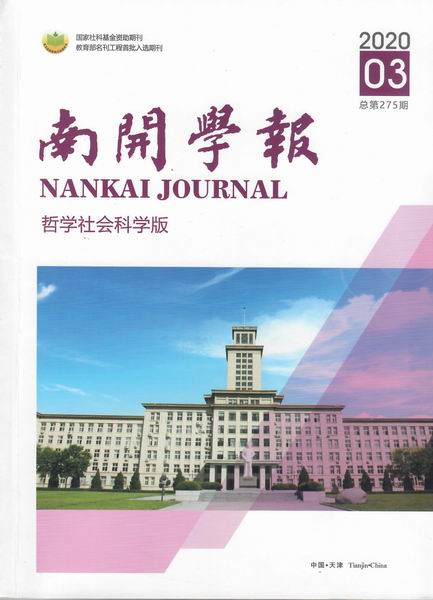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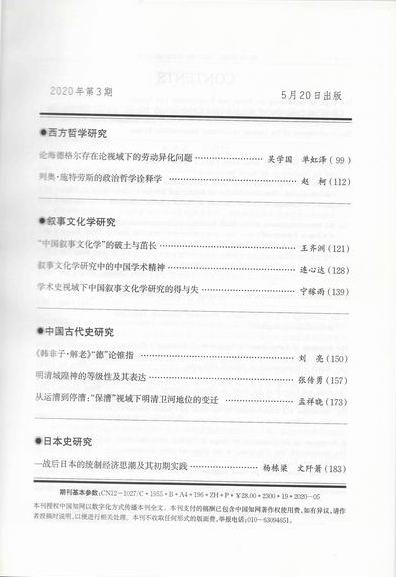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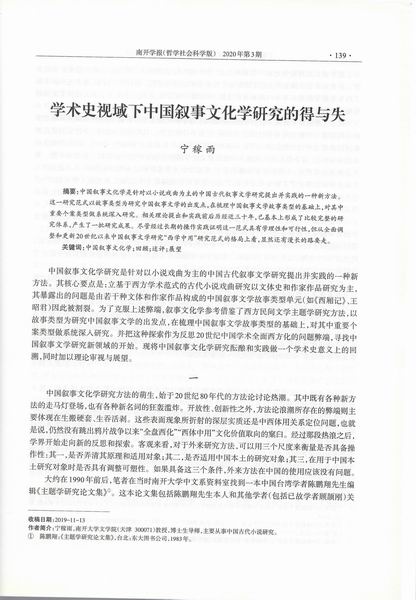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