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
|
2010年2月18日 0:41:02
|
收藏本站 | 设为首页 |

|
|
雅雨说稗
从《古镜记》看唐人“有意为小说”
宁稼雨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说过六朝志怪非“有意为小说”,再来看唐人小说,对其“有意”的感受和认识似乎就更能明晰和真切一些。这里以《古镜记》为特例,说说唐人“有意为小说”的各种角度理解。
一.
首先应该澄清和明确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唐人小说都具有“有意为小说”的品质。在唐代之前,以文言为主的中国小说实际上已经形成几种形态不同但大致成型的题材和体裁品类样式。其中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是六朝时期两大小说主流品类。此外还有以《西京杂记》为代表的杂记体,以邯郸淳《笑林》为代表的谐谑体等。以上四种品类小说在唐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唐代之后也还继续存在衍生下去。但是,这四种小说除了部分志怪小说外,其余几种品类与“有意为小说”关系相对寡淡一些,因为它们本身在书写编纂和文体性质上基本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六朝至唐代唯一一种文体动态变化较大,具有脱胎换骨,推陈出新意义的小说文体是传记(或曰杂传)小说。
唐前时期传记小说大抵从史部传记文章演化而来,写作风格与史书人物传记近似,只是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虽然数量不多,但还是能够自成体系。这类小说始自《穆天子传》,影响比较大的还有《燕丹子》,以及《汉武帝内传》等。与以上其他四类小说相比,这类小说的特点是基本脱离了“丛残小语”式的片段故事摘录,而是更加注意故事和人物的完整性。但基本还是历史人物相关传说故事的汇集,缺少作者的构思意图和手法创新。尽管如此,其相当完整充分的版面篇幅却具备预留了拓展再造的有效空间。所以,所谓“有意为小说”,实际上只是这类小说脱胎换骨,成为唐代传奇小说才具备的文体更新升华的产物。从体制上看,唐传奇分为两种,以人物事迹为描写反映对象的一般称为“传”,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以事件为描写反映对象的一般称为“记”,如《古镜记》《离魂记》《感梦记》等。这类在唐前传记类小说基础上衍化更新出来的传奇体小说,才是“有意为小说”的主力军。
鲁迅所说唐人“有意为小说”的重心是“有意”,其核心含义是“自觉创作”。前文已经述及,六朝志怪虽然不乏非现实内容描写,但基本不是自觉创作,所以难以划入“有意”之列。而唐代传奇小说一方面充分利用六朝传记类小说搭建的完整篇什平台,一方面又主动把小说作为自己反映社会现实,参与、关注并评价社会问题的手段和工具,同时还从志怪、志人等其他品类小说中汲取艺术养分,汇为一炉,开创了中国小说成熟的新天地。这一点,王度《古镜记》具有充分代表性。
二.
《古镜记》精心构思设计的小说结构布局揭示证明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小说与政治的紧密关联。
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与现实社会的关联角度看,文学是关注强度最高的品类,而小说又是其中强度更高的主体部分。晚清时期梁启超甚至把小说的政治作用提升到挽救国家命运的高度来认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个观点已经逐渐为文学理论界吸收,成为文学普遍规律得到认同。一些学者认为:小说通过叙事塑造 “政治想象”,以隐喻、虚构、批判等方式介入现实政治,如政治小说、社会批判小说等,推动思想启蒙与舆论发酵。国外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文学与政治》,国内如南帆《文学与权力》等著作。这些说明小说不仅反映现实,更能通过叙事重构认知、激发讨论,成为政治参与的特殊形式。
古代传记小说作为史部的从属产品,虽然也会不同程度含有编撰者主观倾向的“春秋笔法”,但整篇传记的主要工作任务还是本着史学求实的宗旨,完整交代人物或事件的基本框架过程。唐代小说对于传统传记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作者敢于大胆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情感倾向以艺术构想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关于这个问题,卞孝萱先生曾经有过专门深入研究。他在《唐代小说与政治》《唐传奇新探》两部书中,从文史互证的角度,集中探讨小说与政治的关联,他认为唐传奇等小说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反映唐代政治现实与矛盾的重要史料,具有 “补史”“证史” 的作用;通过分析小说可挖掘正史未明言的政治内幕与权力斗争。比如《唐太宗入冥记》在佛教果报框架下谴责唐太宗,反映 “玄武门之变” 等政治争议;《上清传》涉及牛李党争,可能是李德裕一系为洗刷其父李吉甫、攻击陆贽及其门生而作;《任氏传》《枕中记》等与元载、杨炎、刘晏等权臣间的对立有关;《南柯太守传》《红线》《聂隐娘》等影射藩镇割据;《辛公平上仙》《河间传》等与宦官专权相关。
除了卞先生列举的几例之外,《古镜记》也是一篇作者深含寓意的政治小说。
《古镜记》这篇作品以宝镜为中心线索,将十几个宝镜除灵怪、灭灾异的故事串连在起。故事中的人物,多是确有其人的,如作者王度,其弟王勣等。而故事中经常出现的灵异妖怪,如化成婢女的千年老狸,化为老者山公和毛生的老龟和长狼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作品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灵怪是否有所指?如果有,指的是什么?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各家文学史、小说史皆以为此篇不过六朝志怪余风,所不同者仅在于它能将若干故事连缀而已,诫然,六朝志怪书中的灵怪,未必皆有所指,但是,将十几个志异故事连级起来的本身,就已经说明唐人与六朝人不同处在于其“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既然有意为小说,那末“假小说以寄笔端”(胡应麟语)也是理所当然的,正如鲁迅所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纤牢鬈,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同上)唐人传奇中多有政治寓意,由此推断,《古镜记》中灵怪有所指,至少是可能的。
但是,究竟是否有所指和指的是什么,还必须从作品本身出发,作者如果仅限于对古镜降伏灵怪的叙述,仅仅是“传息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那就跟六朝志怪相同,我们也没有理由进行这种猜测。可是作者为了让人看懂他的意图,在讲述灵异被灭故事的同时,经常对当时政治形势发出哀叹,这就不能不使人把他讲的灵异故事与他所交代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考察他的用意。
作者把故事的起迄时间,准确明白地标明为大业七年五月至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这段时间,隋场帝滥用徭役,大兴土木,自己又荒淫无度,并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同时,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大业七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隋书·炀帝纪》上)天灾人祸给北方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民众带来很大的灾难,各地百姓揭竿而起,一个波澜壮阔的民众起义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隋末民众起义人和路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对此,作者王度深为不满,把民众起义看作是“字宙丧乱”,“天下向乱,盗败充斥”,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孤立地谈论隋末政治局势,而是和消灭灵怪交织进行的,这就使人感到出于对隋末民众起义的仇视,作者一直要剪除的妖乱灵异,实际上指的是隋末风起云涌的民众起义和战争。
如果说作品中的灵怪是指隋末民众起义的话,那么小说中降伏灵怪的宝镜则显然是指以隋炀帝为代表的隋王朝政权。这一点在作品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作者把故事的起止时间安排在大业七年至十三年这一隋末动乱的年代,说明他对这段历史是极为关心的。对于隋末民众起义,作者疾之如仇,并衷心希望象宝镜消灭灵怪那样,把他所认为的“盗贼”加以剪除,把这种“丧乱”加以平治,于是,他一会儿让宝镜照出千年老狸,一会儿又让宝镜击毙蛇精。王勣带上宝镜出游后,更是逢山化险,履水如夷,消灾灭异,无不灵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他心头之恨:也似乎有了这个宝镜,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了。
可是正在宝镜无往不胜,作者以宝镜灭怪——以隋王朝消灭各路民众起义的理想要实现时,故事的情节发展却戛然而止,马上让宝镜消声匿迹了,如果离开作品的政治含义弧立来看宝镜突然消失的话,是十分令人费解的。如果结合作者的政治含义理解,答案则比较筒单而合乎情理了,原来作者正在得意宝镜的神灵时,他突然从理的世界中猛然而回到现实,意识到宝镜固然可以在幻想中听凭自己的驱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现实中的民众起义,却并不象灵怪那样容易被宝镜降伏,而且隋炀帝也远没有宝镜那样的神通。相反,杨坚对隋末民众起义只能是束手无策,他看到自己的统治风雨飘摇,只好以游为名,于大业十二年南下江都,南迁后,杨坚“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若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资治通鉴》卷一八五)这些使作者感到失望痛苦,因为这意味着他政治理想的破灭。所以,他只好在自己的幻想高潮中草草收场,让宝镜离去,并颇具匠心地把宝镜亡去的时间,定在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而据《长术辑要》和《资治通鉴》的记载,这一天正是隋炀帝决定迁都的日子。这就不难理解,作者让宝镜这一天离去,正是象征着隋王朝的覆灭。作者无限感慨地说:“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王室如毁”和“宝镜复去”连在一起哀叹,不是作者偶然所为,面是他把宝镜象征隋王朝的明白写照。
三.
王度用古镜象征隋王朝,用灵怪象征隋末民众起义。以古镜灭怪来曲折表现白己的政治理想。人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不明白地表述自已的政治观点,而要采用这种象征的手法呢?
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看,首先,作者之所以用这种手法是因为他已由隋入唐。顾况《戴氏广异记序)云:“国朝燕公《梁四公记》,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如李庚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据《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七引)可见此书写成于唐初,在强大的唐帝国面前,王度如果公开流露对隋王朝的怀念,即使不遭杀身之祸.至少也要为人所不齿。于是他只能用这种隐晦的方法来曲折表达自己的悲凉,至于他与隋王朝感情至深的原因,书中作者自叙云他曾在隋朝任过御史、著作郎、芮城令,河北道持节等官职,并在任御史时兼著作郎,奉诏撰《隋书》,因故未竞。在一篇虚构的小说中念念不忘地把以往自己任过的职事重新数落一遍,说明了他对这段历史的自豪。其次,作家的创作,有自由选择创作方法的权利,但却不能不受到文学形式自身发展的阶段约缚。中国叙事文学到唐前仅仅是雏形和准备时期。六朝时期志怪的写法是浪漫的,志人则主要是写实的,如果完全用志人的写作方法,这篇小说就无法写作。因为志人小说中的故事,多是生活琐事的真实记录。王度要表现的是理想,而这种理想生活中又是没有原型的。如果完全采用虚构方法写人,就只能象俞万春的《荡寇志》那样,具体地写出民众起义遭到镇压的经过。然面唐初时小说技巧还没发展到这一步。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古镜记》却以移花接木的手法,完成了中国小说从六朝向唐代的过渡和进化。
王度《古镜记》的基本结构体制来自唐前《燕丹子》《汉武故事》一类传记小说,同时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六朝志怪手法。但它对二者均既有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一面,又有脱胎换骨超越的一面。传记小说的基本体式大致源自史书人物列传体,以纪实方式叙述一个人物或事件的完整过程。《古镜记》记述古镜自始至终的完整过程,正与这个套路体式吻合。不过《古镜记》超越传记小说的地方,在于它吸收了志怪小说的灵异描写,因而使原本平实充赡的传记风格,增添了生动新颖的元素,因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而对于志怪体式而言,它又扬弃了六朝志怪的纪实初衷,自觉明确地运用志怪手法去表现一种非现实的神奇力量,为表达主题服务。正如胡应麟所言:“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传记体与志怪体的融汇结合,实现了1+1大于2的效果,完成了小说编撰从“无意”向“有意”的过渡。
四.
因为六朝时期“文笔之分”,小说文体隶属于“笔”的营垒的缘故,因而未能取得文学资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小说从文学艺术性角度得到发展提升的机会。从唐代开始,随着文学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小说的文采表现也受到高度关注,因而推动了传奇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如同鲁迅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中国小说史略·唐代传奇文》)
其实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注意到唐代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突出进步,甚至有人认为,传奇小说是唐代科举考试前举子向主考官展示证明自己才学的重要武器,即所谓“温卷”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云麓漫钞》)这里所说举子“温卷”是否属实,学界还有争议。但即便不能坐实,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传奇小说在唐代炙手可热的的火爆程度。至于赵彦卫对于传奇小说何以火爆原因的总结解释,倒是更加明确点明了唐人“有意为小说”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的成就。
《古镜记》问世于唐代初年,应该与所谓“温卷”之说无关,但它在艺术表现方面的成就,却足可以为赵彦卫的说法增添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古镜记》的“有意为小说”,不仅表现在有明确的主观意图寓意和思想寄托,而且主要还表现在艺术形式的突破了六朝笔记小说的各种束缚,刻意追求新的表现形式上。
第一,六朝志怪、志人小说所记载的故事,都是作者随手记下,各自独立的故事。这些故事之间在时间上和逻辑因果关系上都没有必然性,只是一种散漫的体制形式。王度在小说体制方面的明确意识和成功表现在于:作品以古镜为中心线索,把十几个古镜去灾灭邪的故事连缀在一起,成为一个大故事,为表现个共同主题思想服务。这样就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表现方法,开拓了唐代传奇小说在体制结构方面的完整性,以及重在渲染故事情节的新风气。因为它增大了小说的容量,加强了小说作为文学形式的表现力。
第二,象征手法的使用,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尽管有很多浪漫色彩的志怪故事,但它们本身却都没有什么寓意,更没有什么象征意义。而《古镜记》则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把理想、幻想,现实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古镜暗指隋炀帝为代表的隋王朝,以灵怪代表隋末各路民众起义;以宝镜的得失,象征隋王朝的兴衰,进而表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作者自觉使用的象征手法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思想蕴含的钥匙。
第三,词采华丽,是这篇小说与六朝小说的又一区别,也是它体现唐传奇特点的贡献之一。王度吸取了辞赋和骈文中洋洋酒酒,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并结合六朝小说叙事简略的特点,行文既有文彩又不失之繁缛。如写王勣回述持镜过江南时说:
游江南,将度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撮山曲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迥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鼋鼍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海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
这段文字对于王勣持镜过程的描写,纵横辟阖,大起大落。无论是对于一路险恶环境的渲染描写,还是对王勣出镜照险的游移换景,宛如好莱坞大片的惊险蒙太奇,令人目不暇接,堪称美不胜收, 完全可以跟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一节精彩描写相媲美。胡应麟谈到唐人小说的语言时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清人李慈铭说:“唐人小说,藻采斐然。”(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这些概括用来形容上述引文,不可谓夸张失实。
万事开头难。从六朝时期被文学营垒拒之门外,到唐初主动以华彩文章自觉构思创作传奇小说,以之敲开文学大门,《古镜记》《游仙窟》《梁四公记》这些唐初传奇小说筚路蓝缕,开疆拓土,在从六朝小说向唐中期以后传奇的过渡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扭转风气的重要作用,不应当被忽视。唐人“有意为小说”,也应该为它们记上头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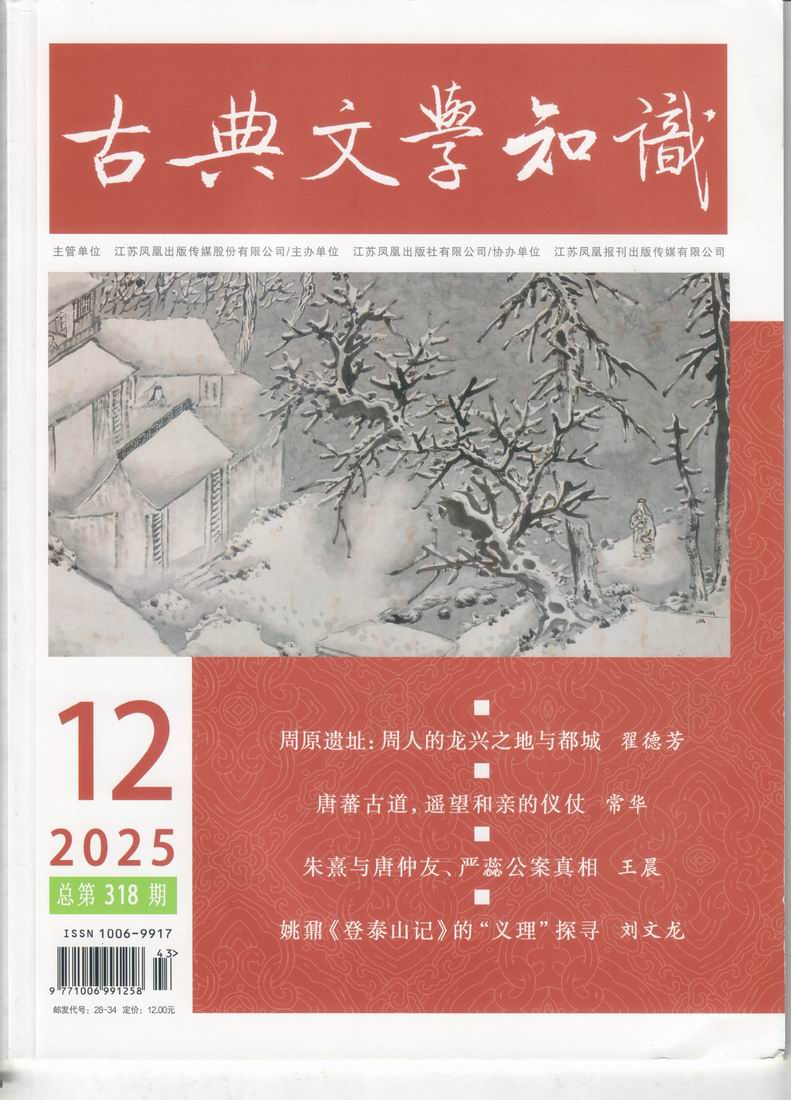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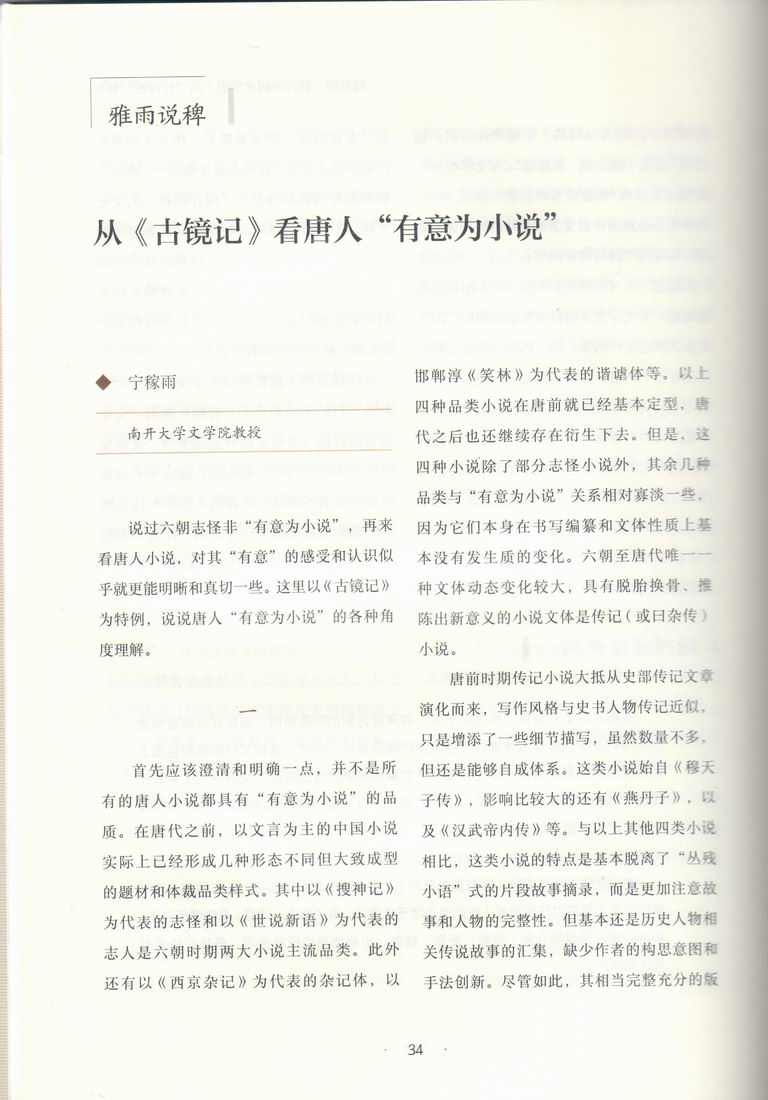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