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
|
2010年2月18日 0:41:02
|
收藏本站 | 设为首页 |

|
|
[摘要] 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中不乏价值评价的要素,这些价值评价要素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诉求。帝王、士人、市民这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三个不同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其中,帝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起步和奠基阶段,其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标准是以“善”为核心的“载道”和“教化”;士人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成熟和繁荣阶段,其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标准是以“美”为核心的“修身”和“怡情”;市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深化阶段,其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标准是以“真”为核心的求真求变。由于评价主体各自社会地位和文学观念的不同,他们在评价要素上所表现出来的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的比重也有很大差别。
[关键词] 文艺评论 价值观念 帝王 士人 市民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三阶段
任何文艺评论都是一种社会活动,都必然带有其所从属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制约因素。同时,文艺评论往往又要以个人身份进行。所以,文艺评论又是在一定社会环境制约下的个人活动,带有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如果社会环境制约因素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话,那么,这种稳定性又不是凝固不变的。所以,文艺评论又是静态与动态相互交错的历时过程。从文艺评论的价值观念角度看,尤为重要的是:“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从其内在结构来看,是以价值思维方式为基础, 以基本评价标准为‘硬核’,包括许多要素在内的一个观念体系。价值思维方式是主体据以形成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思维准则和评价方式。基本评价标准作为文学价值观念的‘硬核’,是文学价值观念的生长点、聚汇点。每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内部都有这么一个‘硬核’,并以这个硬核为中心,直接或间接地派生出一系列文学价值观念来。”[1]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念体系?这些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了哪些价值评价主体?这些主体内部的思维准则和评价方式有什么差异?我以为这是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基础性问题。
笔者认为,20世纪以来从西方学者提出大传统小传统(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理论,到我国台湾学者借鉴这些理论用“雅俗文化”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释,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中国文化的一些深层问题,尤其是不能解释中国古代帝王、士人、市民三个不同阶层在文艺活动和文艺评论活动中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所以,本文以笔者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为理论基础,将帝王、士人、市民这三个不同的社会身份类型作为解读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切入视角。[2]中国古代文艺评论基本评价标准这个文艺评论价值观念的“硬核”之所以会发生动态变化,是由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帝王、士人、市民这三个主要文化阶层群体在文化舞台的主次角色变化所决定的。
本文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从进入文明社会开始,按照文化的社会属性划分,大致分为帝王、士人和市民三个时段。这三个时段和相应主体既是中国社会文化色块交错更替的历时进程,也是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社会基础和评价主体的主要构成。(1)帝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起步奠基阶段。帝王文化的时间跨度大约是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根基就形成于这个时代,其核心是帝王的王权意志。这种政治上帝王轴心的形成和巩固,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都具有强大的制约和影响力。从文化基本建设的主导倾向上来看,整个这段时间的观念体系也是以帝王为主导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以帝王为出发点。帝王文化这个价值评价主体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文艺评论的价值取向必然是为帝王利益张目。中国文艺评论一些最基本的标准导向和评价取向,如“道统观念”“教化观念”“忠君观念”等等都由此派生形成。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标准是以“善”为核心的“载道”和“教化”,其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形式主要是帝王阶层这个评价主体以政治组织形式实现其“载道”“教化”评价标准。(2)士人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成熟繁荣阶段。从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前后大约一千年的时间为文人文化时期。此间,中国文化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帝王文化根基依旧稳固的基础上,以文人学士为主体的中国文人文化开始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它不但催生并完成了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成熟独立,而且还拉开了中国文艺评论走向成熟和独立的大幕。在三个评价主体中,士人阶层对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贡献最大。士人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整体构建者,同时也是“真善美”价值标准中以“美”为内核的价值评价标准在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中安家落户的操作者。(3)市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深化阶段。这个时期从宋代已经开始萌发,主要包括元、明、清三个时代。城市经济的繁荣不仅造就了庞大的市民阶层,同时也直接刺激了广大市民阶层精神文化的需求。这种文化需求直接导致了宋代以后市民文化的繁荣,并使市民文化进入并占据了这个时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市民阶层在中国文化舞台上的登台亮相,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结构。从文学艺术的样式,到文艺评论的方式方法,都出现了全新的变革。以李贽为代表的市民文化代言人,不仅用文学发展史观颠覆了以往的复古文学观,而且以“真”为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标准,提出了与帝王“载道”“教化”评价标准针锋相对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标准。
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体系庞大,硕果累累,其中不乏含有价值评价的要素。这些价值评价要素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诉求。所以,对这些价值评价要素的梳理,需要从不同评价主体的价值评价异同切入。帝王、士人、市民这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三个不同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这是由于其文学价值观念主体差异性所决定的,同时,由于评价主体各自社会地位和文学观念的不同,在评价要素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的比重也有很大差别。所以,从三个评价主体渠道分析中国古代文学评论中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差别,寻找其各自在二者关系中实现兼容和自洽的程度,也不失为一条有效渠道。
二、帝王文化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及其特色
帝王文化的核心是政治文化。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价值评价“硬核”的出发点,具有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其价值评价要素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主要表现在以是否具有“载道”内容和是否具有“教化”功能为基本价值评价条件。所谓“载道”,主要包括“忠君”“颂圣”“修齐治平”等政治社会观念,就是要以此观念去教化世人,这是中国文化最初的本意。《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在先民看来,天文和人文分别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规则秩序的总结。了解天文可以掌握自然规律,了解人文则可以用来教化天下。这样也就为后代社会所有文化活动的目的做了预设规定,文学艺术当然也在其中。如果说西周时期还是一个笼统的意向设定的话,那么从春秋战国之后,随着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的逐渐成熟繁荣,这种以教化为目的的“载道”价值观念也就不断充实细化,成为一种代表官方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的概念范畴。从孔子开始,以忠君为核心目的的“兴观群怨”观念就一直作为官方认可的文学艺术评价标准推行于世。
如果说在孔子那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还只是一种理想的礼制设计图的话,那么,从汉代开始,经过“君权神授”的造神舆论鼓噪,帝王成为天和神的化身,也成为国家的化身,成为封建时代衡量一切事物是非高下的终极标准。从汉代到清末两千多年间,以君权利益作为文学艺术教化目的这个基本的内核始终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和改变。《毛诗序》:“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4]在《毛诗序》作者看来,诗作为一切文学艺术形式的最高代表,其全部责任和价值就在于对民众进行人伦秩序的培育教化。这个思路成为一种定式,规定了汉代以后文艺评论价值取向的基本尺度。一些文学艺术运动和理论主张,也在此内核规定下不断努力拉回他们认为已经偏离的“载道”线路。从唐代古文运动,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再到明清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各种复古思潮,都是对“载道”价值观念在文学领域的不断贯彻落实和重新认识。
在这个基本内核规定下,帝王文化的文艺评论价值要素有着相当严密而有效的评价机制和操作程序。在文艺评论价值观念的表述上,作为评价主体的帝王文化有三种具体评论渠道。
第一是帝王粉墨登场,直接表述代表帝王文化内核价值观念的文艺评论言论。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语是从帝王文化角度对文学艺术的社会地位价值做出的最高估价,表现出帝王这个文艺评价主体对文艺地位价值的最大肯定。这一传统在后来历代帝王那里都得到继承和发扬,牢牢抓住并掌控了用文艺评价导向作为教化工具手段的渠道。
第二是帝王与官僚文人君臣组合,共同探讨设计帝王文化文艺内核价值观念。他们一方面为“载道”的文学价值观念不断变换包装,反复向世人强调和凸显“载道”价值观念的地位,一方面身体力行,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身份,从批评理论和文学创作本身的实绩来引领帝王文化背景下的“载道”价值观念导向。唐代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和周围文臣共同参与了关于文学艺术必须以“载道”教化为目的的文艺价值讨论。史载李世民“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5]他们的这些讨论,尤其是其中关于文艺“载道”这一核心价值观点,散见于这些参与者的各类文章中:“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6](《隋书·文学传序》)“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7](《梁书·文学传序》)“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8](《晋书·文苑传序》)《隋书》的主编是魏徵,《梁书》的主编是姚察、姚思廉父子,《晋书》的主编是房玄龄。除了主编之外,当时一些著名文人都参加了诸史的编纂工作。魏徵和李世民的关系世所公知,其他几位也都是贞观之治的得力帮手。不难想见,这几位重量级文豪也正是李世民“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活动的参与者。而这几篇殊途同归的渲染“载道”教化的文字内容,也应该是君臣“乙夜忘疲,中宵不寐”的共同研讨成果,是他们向全社会发出的文艺评论重要价值评价标准。古代君臣共谋文艺评论“载道”大业,于此可见一斑。受此影响所及,一些官僚文人干脆把迎合君王所好,捍卫振兴“文以载道”价值标准大旗,作为文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伟业的具体实践。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到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大抵如此。
第三是动用国家权力机器,直接参与和掌控文学艺术的价值肯定和否定评判。刘向《说苑·指武》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9]这已经把王道教化和政治处罚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对于颂圣有功,贯彻“载道”观念得力的官僚和其他文人,予以表彰奖励;反之,则运用政治手段予以严惩。从“乌台诗案”到明清各种文字狱,再到元明清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颁发的对于小说戏曲的各种禁毁法令,把国家和政府使用政治方式否定乃至枪毙文学艺术作品价值的举动,推演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不讲学理,直接以权力裁定文学艺术价值甚至夺走文学艺术家生命的做法尽管能起到一时作用,但是,其结果不但在政治上产生民心和舆论损失的严重后果,而且也是中国文艺评论难以从学理的角度构筑完整科学的价值体系的重大障碍,对后代文艺评论实践中类似的越过学理直接进入价值裁决的方式,具有直接的示范效应。
以帝王评价为主体的价值诉求,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价值取向偏向政治统治和道德教化,价值陈述比较笼统直接,价值评价的行政灌输甚至暴力渠道多于学理分析。从中可见,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价值性评价大于分析性评价,因而二者的兼容和自洽也就难以顺畅实现。
三、士人文化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及其评价特色
士人文化的核心是审美文化。士人文化及其文艺评论的出现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门阀士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实力的社会阶层崛起,二是文学艺术作为独立的文化精神活动从其他实用性社会文化功能(尤其是政治礼教功能)中分离出来。这两个前提的出现,既保证了士人作为独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的实体存在,又为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发生的时代性转换,以及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之间的兼容和自洽创造了必要条件。
士人文化文艺评论价值要素的呈现方式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关键的节点是人物品藻活动从人物品评向文艺评论过渡的嬗变承接。人物品藻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它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文艺评论及其价值评价要素的直接影响。人物品藻起源于汉代,本来是一项政府人才选拔的方式。汉代人才选拔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途径。自下而上叫“荐举”,自上而下叫“征辟”。“荐举”和“征辟”的依据就是地方乡里缙绅对参选人员的品评,这是最早的人物月旦评活动:“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10](《后汉书·许劭传》)人物品评从汉代一直持续到东晋,尽管在品评方式上相对稳定,但在评价标准上却随着社会变迁发生很大变化。最终结果,直接导致了士人文化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出现。从人物品评标准来看,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所以人物评价以道德为先,“孝”字为上。曹魏时期天下大乱,诸侯群雄纷起,各路草莽求贤若渴,此时人物品评的标准由汉代“孝”字替换为“才”字。曹操就大声疾呼:“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11]于是,执政管理和军事韬略之才能便成为曹魏时期人物品评的优先价值标准。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两晋时期。司马氏鼎革之后,社会上人物品藻活动在标准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改变了以往人才选拔的机制。人才选拔的依据不再是来自社会舆论的人物品评,而是家族的社会地位。门阀士族操控了官场进退之门,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实,造成“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司马氏政权的高压统治造成“道统”与“势统”的严重分裂。两方面的社会变化导致人物品藻的标准发生重大调整——由汉代以来以官场选拔官员为目的的社会政治标准变为疏离社会政治的审美性标准。对人物自身的审美性品评热潮势不可挡,如同宗白华所说:“一般知识分子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12]
人物品藻活动评价的标准发生变化,对以文人为评价主体的文艺评论价值观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具体途径就是在人物品藻的审美性评价中,加入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评价,使三者相互借用比附,从而大大增强了人物、自然、艺术三者审美的认知度和表现力,并直接导引出士人文化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标准的形成。魏晋之前,中国人对于人物、自然、艺术三者审美关系的认识已经萌发。儒家对于三者美感的认识带有较强的礼制和道德教化色彩以及实用功利目的。道家在艺术审美的自觉程度上要超过儒家,庄子对藐姑射仙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的赞美描绘中,已经开始采用自然美和人物美相互比喻的手法。《离骚》中也熟练使用了香草美人手法。但他们对三者美感特征和相互关系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还没有从美学和价值评价的角度来认识把握三者的关系。魏晋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崭露头角,几乎垄断了社会舞台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的所有市场份额。从文化方面看,士族文人的人格独立和文学艺术自身独立这双重因素决定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左右和引导当时社会的文艺评论价值导向。人物品藻活动不仅大大开掘了社会对人物美的认识层次,而且还把对人物美的品评方式和评价标准移用于自然美和艺术美的评价,实现了审美性人物品藻标准向山水诗创作和文艺评论价值标准的移植转换。创造和转换的契机在于,当人们苦于用精准确切的语言来进行人物美的描述评价时,想到了用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描述评价作为替代。如人物品评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借用自然美的语词有“瑶林琼树”“璞玉浑金”“龙跃六津”“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九皋之鹤鸣,空谷之白驹”等等。通过自然美的描述,人物美的内在精神境界和气质美感得到彰显。有了这样的评价经验积累,艺术美也可以用自然美来比喻形容:“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桓即赏以二婢。”[13](《世说新语·言语》)顾恺之身为大艺术家,当然深得艺术个中三昧,面对桓温的悬赏,他能信手拈来,用红霞这一自然美景来形容江陵城建筑艺术。艺术修养之深,可见一斑。于是,人物美、自然美、艺术美三者之间概念难以表述的美感通过相互比拟得到了形象提示,因而获得艺术通感的实现。三种美的评价相互借力,从而使评论价值从内涵到形式都得到了清晰呈现。士人文化以审美价值取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也由此生成。
除此之外,人物品藻的评价程序和标准设定,也直接为士人文化的文艺评论价值标准评定提供了具体规范和范式:“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14](《世说新语·品藻》)故事告诉我们,东晋时期的人物品藻活动中,人们把温峤列入二流上品。每次品藻活动人们谈论一流人物即将结束时,温峤脸上总是非常窘迫。这就涉及到了人物品藻活动的品评等级划分的具体程序。此法渊源于《汉书·古今人表》。该表以古代人物为经,以品第人物为纬,按九品分为九栏。根据表序“上智”“下愚”的理论及表所分的具体情况来看,品第标准,是以人的品行为主,参之以事功的大小和学术的高低。这种形式在曹魏时期吸收依据汉代以来以乡里人物品藻为基础的“荐举”“征辟”人才选拔制度,改造成为“九品中正制”(九品官人法)。其内容是将参评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个级别。这也就是魏晋人物品藻活动根据“九品中正制”将《汉书·古今人表》这一书面文字的人物品行等级划分标准用之于现实的人物品藻活动中,将品藻的对象按既定标准的程度差别分为九个档次级别规则范式的由来。从六朝开始,在以审美取向为价值评价标准,以优劣程度为区分条件的人物品藻活动直接影响下,按质分品、以品次第的方法成为士人文化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一直沿用不衰的固定评价形式。
较早采用分品形式进行文艺评论的是南朝梁谢赫《画品》。《画品》完全依据以审美价值为标准的人物品藻分品形式,按作者理解的画家作品价值高下,分为“六品”(六个档次级别),其品第原则是:“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然迹有巧拙,艺无古今,谨依远近,随其品第,裁成序引。”[15]从谢赫的宣言中可以看到,如同人物美的高下需要品第一样,绘画作品也需要按照审美价值的高下进行品第。与谢赫大约同时的南朝梁钟嵘《诗品》则是文学评论领域采用人物品藻的审美评论方式,从审美角度进行诗人价值评价的发轫之作。钟嵘在《诗品序》里,将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评价原则定义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16]从文中内容可见,钟嵘是把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以及内在的风力与外在并举作为诗歌艺术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在此标准下,钟嵘《诗品》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其中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
如果说人物品藻按次品第的方法为后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提供了外在范式方法的话,那么,人物品藻活动对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观察挖掘和精准评价则为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找到了最核心的评价焦点,二者结合,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以鉴赏为价值评价主要形式的直接渊源。
汉代以来兴起的人物品藻活动,推广流行于全国各地,在参考吸收先秦以来包括相术在内的各种人物观察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一整套严密周祥的方式方法。这些方法集中表现在曹魏时期名家学者刘劭《人物志》一书中。该书全面总结了汉代以来人物品藻活动的各种方式,提出以“平淡无味”为核心的人物品评最高价值标准,不仅成为魏晋玄学“贵无”学说的主要理论来源,而且为后代士人文化背景下以价值认知为文艺评论取向规则奠定了坚实基础。刘劭在《人物志》中提出,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为“五德”。也就是说,从气质层面看,人的自然气血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徵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徵”。在才性方面,刘劭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等三类。透过德、法、术等三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十二才”(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担任不同的官职。刘劭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评价和拔选人才的标准。刘劭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澹无味,是为圣人。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澹”与“聪明”两种层次,聪明为才,而平澹则是生命所展现的境界,已不单纯是道德修养和社会实用的层次,更是对人性内在本质的审美把握和审美评价。
刘劭对于人物品藻活动通过各种方法渠道认识把握人物内在品德性格,进而达到带有审美意义的价值判断,这一思路大大影响了文学走向独立过程中士人文化以审美为内核取向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首先受其影响的是刘勰《文心雕龙》。作为第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文学批评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书中很多涉及到作家个人修养和作品价值评价的部分,内容都与人物品藻的范畴概念和价值评论方法有关,明显有人物品藻活动及《人物志》影响的痕迹。从《体性》《才略》到《神思》《情采》,人物品藻氛围气息迎面扑来。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知音》篇有关文学批评鉴赏的内容。该篇从知音(文学批评)之难入手,提出文学批评的具体方法,进而总结文学批评的规律原理。其中两个重要核心点完全来自对人物品藻活动的借鉴发挥。其一是借用人物品藻方式,提出文学批评的“六观”方法:“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17]对比一下刘劭《人物志》从“九徵”到“十二才”的各种观察评价人物方法,就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其二是对文学批评原理的总结:“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18]如同审美性的人物品藻需要从外貌入手,逐渐洞悉把握其内在精神气质再作出评价断语一样,批评者需要“沿波讨源”“觇文见心”,方能“披文入情”“虽幽必显”。“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知音》篇最后关于文学批评的原理陈述,完全是借用人物品藻的语言表述方式,来说明文学批评通过何种方式渠道,才能最后达到“见心”“入情”“达理”这些从学理层面进行审美性文学评论的士人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评价内核。可见,到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士人人物品藻活动以审美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评论方法,从整个体系框架到具体方式范畴,已经完全为中国文学批评所吸收,形成了一套以审美判断为基本价值取向,以范畴分类为价值区分方法的士人文化文学批评价值评价方法。这一方法范式经过《文心雕龙·知音》的定型,成为一种规范,对后代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方法产生直接的规定和影响。司空图《诗品》将诗歌审美范畴区分为二十四种: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严羽《沧浪诗话》所分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等五种诗法,以及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等九种诗品,都是这种审美性文艺评论价值评价范式的成功再现和演示。
这样,从谢赫《画品》、钟嵘《诗品》,到刘勰《文心雕龙》,就从晋代审美性人物品藻那里接过了从审美角度进行人物价值评价的理念方法,并成功移用于中国文艺评论,把文艺作品的审美性评价作为一个固定的范式确定下来,为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中士人文化以审美为内核价值评价形式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影响并规定了后来士人文化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形式。这个内核的基本构成就是以审美评价为核心,把人物品鉴的方法转换为文学鉴赏的方法,形成中国古代士人文化背景下文艺批评的独有方式和固定传统。正如宗白华所说:“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19]
相比于帝王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以“载道”“教化”为基本内核的价值评论标准和主要通过官方行政渠道进行价值评价标准宣传的方式渠道,士人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内核转而为审美,方式则主要集中在人物品藻基础上的审美鉴赏。同时,士人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框架有较强的体系感和科学性,基本上是从学理研究分析的角度进行,相比于帝王文化背景下某些越过学理直接用政治褒贬进行文艺评论价值判断的方式更具有真理性的含量。因此,其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之间的兼容和自洽程度最高,最为成熟。
四、市民文化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及其评价特色
市民文化的核心是实用文化。从需求的动力来看,帝王文化通过政治手段达到“载道”和“教化”目的是出于专制统治的需要,士人文化以品鉴方式达到审美目的是出于士人 “修身”“怡情”的需要,而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载道”“怡情”都是很遥远的,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的现实生存问题。市民文化从文艺样式到价值诉求再到文艺评论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化舞台的底色,在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文化风貌和价值标准。
第一,关于市民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主体构成和时间跨度问题。从时间上看,市民文化大幕正式拉开是从元代开始。但宋代市民文化文艺创作和评论均已初具规模,为元代开始的市民文化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从市民文化背景下文艺价值评论主体构成来看,市民阶层与其他两个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帝王和士人)有所不同。由于自身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的限制,市民阶层自身难以完成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为目的的文学艺术创作及其价值评价工作。所以,市民文化的创作和评价需要借助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一方面,他们需要借助帝王文化基本内核作为包装,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吸引帝王文化的眼球,取得自身存在的社会认可;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士人阶层中的代言人,所以,士人中地位和感情倾向于市民阶层的文人往往成为市民文化文艺创作和价值评价的执行者,从罗烨、李贽,到冯梦龙、金圣叹等,均属此类参与者。有了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市民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才是完整和有效的。正因为有以上因素,市民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内核形成路线,是从较为单纯的市民文化色素,逐渐转入以市民文化求真求实为主,部分融入士人文化的审美要素和帝王文化的教化要素的汇通之路。
第二,关于市民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对象的转换认识问题。帝王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是“载道”和“教化”,士人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是“审美”和“怡情”。尽管二者在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取向的内核上取径不同,但评价对象却基本同一,都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代表的传统主流文学样式。市民文化在此背景下登台亮相,遇到第一个障碍就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的载体渠道问题。对于市民阶层来说,诗歌、散文这些传统主流文学样式不?鲇薪邮芎痛サ睦眩宜且丫弁跷幕褪咳宋幕倏芈⒍希晌锔髯晕幕咔蟮拇醋髑篮图壑灯兰鄱韵蟆2唤鋈绱耍谝酝奈幕杼ㄖ校硎忻窕蛳虏忝裰谖幕粜缘男∷怠⑾非雀髦滞ㄋ孜难问揭丫坏弁跷幕褪咳宋幕穸ā⒈岬投τ谖幕杼ǖ拿磐狻K裕忻裎幕胍翘萌胧遥蔽裰本褪且岣叻从匙约航撞阄幕?/span>的各种样式载体的社会地位。在此背景下,市民文化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首要工作就是改变各种通俗文学样式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重新评价各种通俗文学样式的作用价值。这一工作从宋代市民文化刚刚起步时就已经开始了。罗烨《醉翁谈录》:“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举断模按,师表规模,靠敷演令看官清耳。”“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蕴藏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20]与此前帝王文化和士人文化的文艺评论价值观念中对于小说的蔑视歧视态度相比,罗烨对小说价值和小说家艺术修养的分析评价令人耳目一新,完全反映出一个新兴文化舞台对于自己舞台主角的高度评价和热烈鼓励,体现出一种全新的文艺评论价值取向。正如宁宗一所说:“罗烨《醉翁谈录》中敢于突破统治阶级鄙视通俗小说和小说家的偏见,把小说家的才识和一般人心目中的大学问家并列,确是非常大胆而卓越的见解。同时这也多少反映了市民阶层为自己喜爱的文学争取地位的要求。”[21]这种对于通俗文学样式给予合理的社会地位和正面评价的趋势到了元代之后得到更加广泛的呼应和更加学理化的论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贽的进化文学史观。与罗烨相比,李贽不止是单纯直接肯定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价值,提高其社会地位,而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所谓天下“至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这就不仅以科学的态度,从学理的角度指出小说、戏曲理应成为当时社会文化舞台的主角,充分肯定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社会价值,而且也有力反驳了前后“七子”站在复古立场,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静止文学史观,为转变传统世俗观念,科学地阐释小说、戏曲成为文化舞台主角的道理,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经过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取代诗歌、散文的主角地位,成为元明清以来文学舞台的主流文体和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主要对象的浩大工程,已经基本就绪。这等于为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内核从士人文化背景下的“审美”“怡情”转向市民文化背景下的求真求实,扫清了障碍,搭建了基本平台。
第三,市民文化背景下以市民阶层利益和观念为基本出发点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内核逐渐形成。宋代以来尽管社会变动很大,但城市经济在社会的动荡中却不断增长繁荣,反而刺激了市民阶层的膨胀,促生了市民文化及其价值评价内核。这个内核是建立在肯定市民阶层生存需求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肯定真情实感的表现、以“真”为核心的文艺评论价值取向标准,其内容主要包括:以王学左派(泰州学派)关注百姓日常生活的思想为基础,将其引入文艺评论领域,把肯定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百姓正常生活和生理需求作为文艺评论的正面价值要素。这一文学思想潮流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反映,就是通俗小说的题材从帝王演义、英雄传奇、怪异神魔向世情题材小说的过渡。南宋说话艺术传有“四家”之说,它们各自形成不同的题材类型,并且对明清时期长篇章回小说的题材流派直接产生规定性影响。其中“讲史”一家演化成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系列,“说铁骑儿”一家演化成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说经”一家演化成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小说”一家演化成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这一系列的世情小说。[22]四类小说题材流派的消长明显呈现逆向走势。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走势一致——巅峰在前,仿作续之无力,呈强弩之末态势。相反,世情小说则后发制人,“小说”家在南宋说话艺术时期只是一种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故事的总称,罕有其他三类中含有的经典性的佼佼者。但从明代后期开始,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小说突然喷涌而出,既有《金瓶梅》之类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有《三言二拍》之类的短篇拟话本小说。到清代,其他三种类型的小说虽然数量不少,但精品难寻,而世情小说却依然后劲十足,变异演化出《儒林外史》《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巨著。十分明显,小说创作舞台的这个巨大转变,正是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是道”民本思想在文学舞台的落实和实践。
面对这场文学题材的重大变革,那些愿意为市民文化代言的批评家以敏锐的目光抓住这些文艺变革的重要成绩,及时给予正面肯定和价值认可。对于《金瓶梅》这部明代世情小说奇书,明末著名学者谢肇淛慧眼评价道:“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蝶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验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怡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駥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23](谢肇淛《金瓶梅跋》)谢肇淛所列举的《金瓶梅》题材范围,几乎涵盖了市民文化视角所关注的各种社会题材的全部。在肯定《金瓶梅》题材的广泛性之后,谢肇淛将其艺术效果赞美为“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的高妙境界,并且进一步将其定位为“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的上乘之作。与之相类,抱瓮老人对《三言》《二拍》两部拟话本小说也做了全面的价值肯定:“墨憨斋增补《平妖》,穷工极变,不失本末,其技在《水浒》、《三国》之间。至所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戮目。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即空观主人壶矢代兴,爱有《拍案惊奇》两刻。颇费搜获,足供谈座。合之共二百种。”[24](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如果说文学价值生成的重要标志是其以审美的形式表现出现实生活的功利价值的话,那么,从谢肇淛到抱瓮老人,其共同一点就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抓住从《金瓶梅》到《三言二拍》对于它们各自反映的生活功利价值的“恰当处置”:“文学在反映表现生活之时,对事物与现象中的复杂的价值内蕴必须恰当处置,才能生成自我价值。所谓恰当处置,是指文学必须立足于反映事物的审美价值但又不排斥、不违背其他众多的功利价值。”[25]这样,市民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关注、肯定现实世俗生活的价值内核就宣告形成。
第四,市民文化背景下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方式渠道。由价值评价内核和通俗叙事文学文体所决定,其价值评价方式渠道也充分体现了面向市民文化的主旨特色。市民阶层文艺价值评价主要方式渠道为通俗小说戏曲评点、序跋、笔记短文三种方式。三种方式源头均来自传统士人文化圈,但序跋和笔记短文并非市民文化独有的评价方式。而评点虽然源自士人文化圈,但在市民化文人的努力打造下,几乎成为市民文化文艺评论价值评价的独有利器。评点的形式古已有之,其中也含有某些人物品藻中人物评价的形式特征,但成为文学评论的专有形式则始自唐代以来的诗话。不过,和品鉴形式的主流态势相比,评点在诗话领域的发展非常有限,却在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领域获得无限生机,成为通俗文学评论的主要形式。评点在小说领域的落脚始自南宋刘辰翁对于文言笔记小说《世说新语》的评点。在传统帝王和士人文化背景下,文言小说的社会地位介于文史与白话通俗小说之间。与白话通俗小说相比,文言小说还属于正统主流文体范围;但在正统主流文体范围内,文言小说又处在末端。这个地位对于将诗话中的评点方法移至白话通俗小说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位置。刘辰翁是一位稔熟并以评点见长的文学批评家,他在传统文史领域有过诸多评点著作,如《班马异同评》《批点孟浩然集》《批点选注杜工部》《评点唐王丞集》等。而《世说新语》是六朝以来文人雅士趋之若鹜的热门书,刘辰翁以之为评点对象自然是顺理成章。但他始料不及的是,《世说新语》的小说文体身份使其成为评点这一传统诗文领域文艺评论的方式渠道为通俗小说戏曲所用的发轫点。在刘辰翁的带动下,明清时期小说戏曲评点如同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从李贽到金圣叹、脂砚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通俗小说戏曲批评家所采用的评价方式几乎殊途同归地选择了评点。这就说明,评点这种文艺评论方式有其更适合市民文化的评价主体用来表述自己价值标准和好恶取向的优势。这正如清初张潮所言:“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余。或评其事而忼慨激昂,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敢谓发明,聊抒兴趣;既自怡悦,愿共讨论。”[26](《虞初新志·凡例》)这里提到的各种有感于作品内容而产生的评价表达方式,其共同特点就是随感而发,自由畅快。这与帝王文化“载道”的沉重和士人文化“怡情”的含蓄相比,更能体现出市民文化从内容的通俗质朴到评价方式的简洁明快特征来。它用来评价市民阶层关切的各种现实生活问题题材和从市民角度审视历史的观念等,显然更能得心应手,随感随发。
从文艺评论中的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比重来看,与帝王文化评价主体相比,市民文化背景下的文艺评论其分析性评价成分超出价值性评价;与士人文化评价主体相比,无论是其分析性评价和价值性评价的比重,还是整个价值评价体系,都相对较弱。
责任编辑:王法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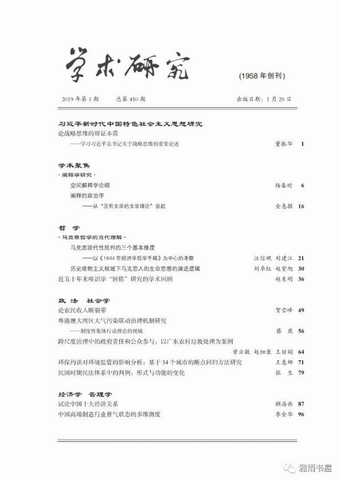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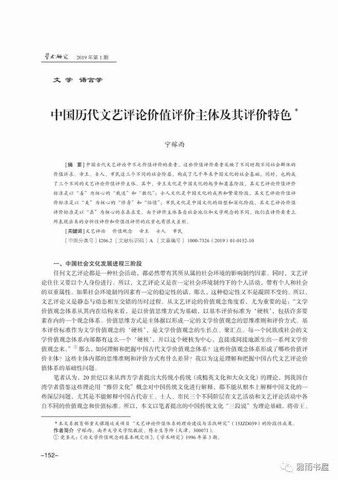
(本文原载《学术研究》2019年第一期)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