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
|
2010年2月18日 0:41:02
|
收藏本站 | 设为首页 |

|
|

一、引 言
《水浒传》问世以来,得到了全民族的喜爱。这个立论,并不因为它曾遭过禁毁而被否定。相反,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不光人民群众爱读《水浒》,统治阶级一样对它爱不释手。首先,统治者对小说戏曲这些通俗文学的爱好程度,并不亚于人民群众,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明成祖时御修《永乐大典》,以很大的篇幅,著录了平话、杂剧和戏文。在此风气下,《水浒传》当然也不例外。明刘銮《五石瓠》卷六:“神宗好览《水浒传》。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徵也。”

什么原因使得《水浒传》得到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一全民族的喜爱呢?这个问题,只有更新方法,变换角度,才有解释的可能。
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以实地考察为主,但并不排斥利用文献资料的方法,尤其对民族史的研究,更应较多地利用文献记载的材料。既然如此,文学史(包括古代作品)的研究,应与民族史的研究相结合,互相提供方法和材料的借鉴。
研究种族团体的心理特征,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对文学作品中种族团体心理特征的研究,目前还只停留在理论号召上。
《水浒》的研究者对作品的“义”多有论及,但往往流于一般性的论述。对“义”
的深层蕴含,这些蕴含与传统思想和民族心理关系如何,似乎还苻进一步揭示的必要。
这几方面撞击的结果,就是本文撰写的缘由。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种族团体的心理特征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心理特质,包括民族性格、习惯、传统、风俗等,它具有相对的稳定件;二是情感范围,主耍指人们的情绪、兴趣等,它比心理特质要活跃一些。
所谓民族性格,既不是无数个性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个别性格的“以一代十”,而是种族团体所共有的性格,即个人性格中属于团体的那一部分。按照这个规定,《水浒传》中民族性格似有这样一些特征。
一是抱打不平,也就是对生命和利益受到威胁的人们,予以无私的各种援助,尤其是武力。抱打不平作为一种心理特质,是一种精神现象,它与意识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它还没有经过逻辑的抽象,成为一种思想,而只是一种潜在的思想因素,但是,这并不排除它受到意识形态诸因素影响的可能性。我认为,抱打不平的心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历史上“侠”的思想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侠”已经作为一种思想形式而被记载下来。

《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见侠与儒是并存而立的。《史记》专列《游侠列传》,记载了荆轲等人的豪侠事迹。到了唐代,这种思想更加流行和发展。李白的思想中,游侠意识占有很大成分。“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龚自珍《最录李白集》)这个时期传奇小说中,出现了大批的侠客形象。如虬髯客、红线、聶隐娘等。以抱打不平为中心游侠思想的出现,源之于社会的动乱。因为只有社会上存在不平之事,才会有人出来抱打。所以,不平的社会,不仅是游侠思想形成的原因,也是《水浒传》中抱打不平性格特征产生的根源。应当指出的是,这种不平之事,决不仅仅限于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象高俅、高衙内等的为非作歹,而且还包括社会上其他分子,甚至包括起义军内部个别人对别人的危害。前者如海闇黎、潘金莲等人,后者如王伦等。因此,《水浒传》中抱打不平的性格,已经超出了阶级斗争的范围,具有一定的民族内部善恶斗争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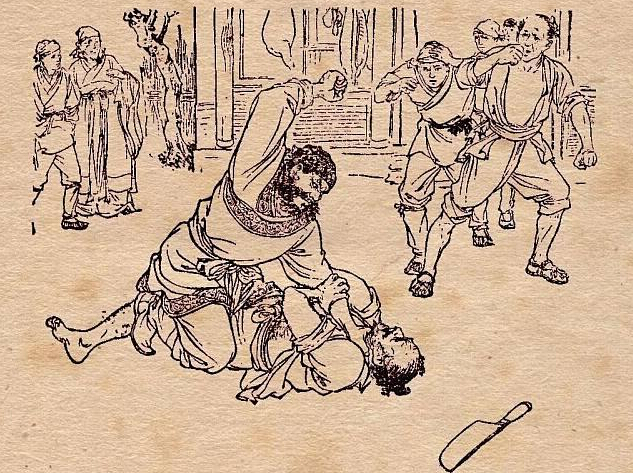
在梁山好汉中,抱打不平是他们共有的性格,他们几乎每人都有一段抱不打平的故事,他们"替天行道”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这种性格的集中表现。尽管梁山好汉中各人的出身不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惊人地一致。出身下级军官的鲁达,听到金老父女的不幸遭遇后,不禁大怒。虽与他无关,但他却勇敢地承担了解救金老父女和教训郑屠的义务。当晁盖等人因劫取生辰钢而面临被捕的危险时,宋江挺身而出,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掩护晁盖逃走。李逵在这方面的性格则更为突出,独劈罗真人,下井救柴进,都是这种性格的反映。尤能说明问题的,是他险些误杀宋江。有人冒充宋江抢夺了刘太公的女儿,李逵信以为真,回到梁山泊,立刻睁大了眼睛,拔出了板斧,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得粉碎。并挥动板斧,抢上忠义堂,要杀宋江。从李逵这个行为中可以看出,为了除邪扶正,扫尽不平,他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不惜撕破兄弟结义之情。

梁山好汉有两次较大规模的行动,集中表现了他们集体的抱打不平性格。一是到江州法场,劫出宋江和戴宗;二是全伙到大名府劫出卢俊义和石秀。这两次事情的起因,开始时与梁山好汉多少有些关系,第一次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而被捕入獄,判为死刑。如果没有私放晁盖一事,宋江也不遭此不幸。第二次卢俊义的被捕,是由于他被赚上梁山,住了很久,因而被人告发入獄。梁山好汉的行为,自然有对自己以前行为负责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情宋江和卢俊义的不幸遭遇,特别是痛恨黃文炳和李固的奸谄和无耻行为。在这两次行动中,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当然包括蔡九知府和梁中书,但他们想除掉黃文炳和李固夫妇的念头,甚至要超过蔡、梁二人。因为这两次事端,是由于这二人的无事生非而造成的。这就可见他们抱打不平的性格特征对阶级界限的跨越。

梁山好汉出身的广泛、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他们抱打不平性格的民族意义。另外,从作品本身看,具备这种性格的,也并非仅仅梁山起义英雄。如武松为武大郎报仇过程中,郓哥和何九叔的行为,就表现了这种性格。不过他们这种性格的表现形式,与梁山好汉不同。由于他们不具备与不平势力抗衡的力量,所以他们只能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去表现这种性格。乔郓哥向武大郎报信,并协助其捉奸,并不仅仅为了报复王婆,而是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武大的同情和对西门庆、潘金莲无耻行为的愤慨。当武松回到阳谷县后,郓哥又积极向他汇报情况。何九叔虽不满于西门庆的行为,但为保身起见,只能敢怒不敢言。但他是个有心人,抱打不平的心理因素使他默默地保存了二块武大的尸骨一一二块被毒后变黑的尸骨。这是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罪证。并将这两块尸骨交给了武松,为武松报仇提供了证据。

《水浒传》中民族性格第二个特征是重友情。重友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代很早就被充分注意。《周易》:“二人同心,其义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论语》:"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末学,吾必谓之学矣。”又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敞之而无憾。”这种意识,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与人为善”思想观念的反映。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他们必然要和别人发生各种联系,这种联系的好坏,与其处境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中国人似乎早已注意到了。《释名》:“人,仁也。”可见在汉代人对人的设计中,就开始注意到单个的人与社会其他人的联系。因为这个“仁”字,就是人们之间相亲相爱的意思。有趣的是,这个由二个“人”组成的字,已经形象地告诉了人们这种人们相互行善的意义。因此,《毛诗》云:“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也。”到了宋元时期,人们在频繁的经济交往中,越发认识到友情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人们看了《清明上河图》会鸟瞰地感到没有友谊,就难以在这繁华的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话,那么以《水浒》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则象一幅剖视图,直接向人们展示这种交往的动机和形式。

《水浒传》的作者,似乎是有意在肯定友情、歌颂友情。这尤其表现在宋江和柴进这两个人身上。作品写宋江“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穀,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如土!人向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危。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第十八回)在第九回作者又借店主人口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专一招接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咐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当柴进与身为流配犯人的林冲相遇后,竟然“滾鞍下马,飞近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然后又拉到庄上,盛情款待。这种重友情的心理特质具有三种社会功用,其一,把这种与人为善的行为溶解为一种心理模式,实现心理境界的自我升华,道德的自我完成。孔子以“仁”解“礼”,把《周礼》中对人们行善的外在规定变成了人们心理横式中的自觉意念。重友情正是这种心理模式的一个方面(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二,有助于事业的成功。宋江既无林冲、武松等人的武功,也逊于吴用的计谋,但他何以成为一百零八人的首领,应该说,正是他重友情、讲义气的性格,使他在好汉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因而他能把好汉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替天行道”。第三,对个人有利。象柴进这样的大地主,本来与起义军无缘,既不会投身起义,也不会得到义军帮助。可当柴进在高唐州被捕,以命危在旦夕时,梁山好汉争先要去救他。最后宋江说服了晁盖,自带八千人马,二十二头领下山救柴进。为了救他,梁山泊又几经周折,搬回公孙胜,才破了高廉的妖法。而李逵又冒着生命危险,下井去救奄奄一息的柴进。如果柴进不重友情、交朋友,对梁山泊无恩,恐怕不会有此报达。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也正是这种心理模式的反映。

第三个性格特征是中和。这是中国民族性格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几乎任何一个受汉文化影响的人都多少会具有一些这种性格。它的思想基础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孔子从“仁”的核心出发,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主张“和为贵”。《礼•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认为中庸是人们道德的极至。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这种“人和”的思想,作为一种哲学伦理思想,潜移默化地然而是牢牢地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灵上。《水浒传》中很多这方面的描写。

先来看梁山英雄之间的“人和”,这一点似乎很简单,梁山人既要聚义,就不能不和。其实,由于他们出身、经历、秉性、地位各不相同,要团结一致,十分不易,然而他们却做到了。其原因,除了政治目标的一致和“聚义”的大旗外,希望人和的心理也占很大成分。《水浒传》写了很多英雄之间先发生误会,然后又和好的故事。如宋江刺配江州,路经揭阳岭时,先被穆弘、穆春兄弟赶得穷途末路,嗣后又在浔阳江上险些吃了张横的“板刀面”。后经李俊出面调解,穆家兄弟和张横都拜在宋江脚下,和好了。十字坡孙二娘本想以蒙汗药麻倒武松,被武松识破打倒在地,张靑出面,认出武松,双方又和好如初。梁山泊在“人和”问题上甚至有过斗争,最后以“人和”派获胜。第一次是王伦嫉贤,被林冲火并。第二次是杨雄、石秀上山。时迁因偷鸡被祝家庄捕获,杨雄、石秀逃上梁山。不想晁盖大怒,令人将杨、石二人斩首,为山寨雪耻。这时,梁山大多数人都站出来反对晁盖的作法:先是宋江出面,把晁盖注意力引向攻打祝家庄,然后是吴用说:“公明哥哥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戴宗也说:“宁可祈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众头领力劝,晁盖方才免了二人。”(四十七回)

再看梁山人与市人之间。他们相互之间都有和睦相处,不愿多事的心理。如三十八回李逵带上宋江给的十两银子去赌錢,想贏了后請宋江。结果输得一塌糊涂。一气之下,李逵不但抢回了自己的十两,又抢了别人的十几两银子,被宋江、戴宗喝住,令其还回。“宋江便叫过小张乙前来,都付与他。小张乙接过来,说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这十两原银虽是李大哥博输与小人,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省得记了冤仇。’”宋江和小张乙的行为,都是不愿多事树敌、希望和平共处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至于杨志杀掉牛二,宋江手刃阎婆惜,都是在多次求和而不得的情况下,被迫杀死对方,同样能说明这一点。
在梁山泊与统治者之间,这种“人和”的心理经过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朦胧到明确,从上到下的发展过程。梁山泊的受招安,除了他们阶级、时代的局限外,“人和”的心理不能不说起到重要作用。宋江作为起义军首领,的确率领义军与宮兵展开了各种斗争。可是,与封建最高统治者和解一一受招安的心理,一直作为一种潜意识镌刻在他心灵深处,并且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第三十二回写武松要去二龙山投鲁智深、杨志,宋江对他说:“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魯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靑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五十九回写宋江凭借强大的武力,跟宿太尉借金铃吊挂,应是威风瘭凛,可他却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然后再提出借金铃挂的請求,这哪里是义军首领对自己俘虏命令式的要求,分明是一位虔诚教徒的忏悔,分明是为以后招安留一条后路。这两番话由于与气氛、环境不符,因此有点象犯神经似地滑稽可笑,但它却是宋江真实心理的流露。

如果说这时宋江与统治者和解的心理只是作为一种潜意识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话,那未菊花会上《满江红》一词,则是这种心理的自觉的表露。作用于这种“和解”希望的,除了传统的思想外,不贼不王的现实也使他幻想能成为封建社会的奴隶。“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转引自《现代西方文论选》)。另外,从道德伦理思想来看,宋江对朝廷“和”的心理,还与“忠”的思想有关。梁山其他好汉的“人和”心理,除了“忠"的思想作用,即在封建统治者容纳自己的前提下,尽量与它和平共处之外,更大程度上是受“义”的思想左右,也就是从“义气”出发,违心地接受宋江等人的投降主义路线。首先,在一部分梁山好汉中,他们上山的动机,并不是主客观一致的结果。他们主观上不愿意上山,只是客观环境的逼迫,才不得已上山。除宋江外,卢俊义、杨志、呼延灼、关胜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人阶级地位较高,属于统治阶级行列的成员。如果没有意外变故,他们十分乐于安其现状,与统治者共处一体。这就是这部分人上山比较困难,舍不得与原阶级告别的原因。而一旦上山后,“义”字成为调整他们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使他们原先“人和”的心理又增加了浓度。不仅与统治者没有割断下意识的心理联系,又要重新考虑好汉之间的和睦问题。而在“八方共域,异族一家”的水泊梁山,大家一致要求思想与行动保持一致,否则,“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笫七十一回)正因如此,虽然有人反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可“义气”规定下“人和”的潜意识使他们还是违心地接受了招安。就连李逵这个坚决反对招安的人,在小说结尾虽然“反心未除”,但这种反心并没战胜“人和”之心,不能使他与宋江撕破脸皮,另立造反大旗,而是表示“死后做哥哥一个小鬼”,甘愿被宋江用药酒夺去自己的生命,和心胜利了。可见,“中和”的性格,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下面简单谈谈以上三个方面之间以及它们与“义”的关系。从纵的方面看,上面三个性格特征与“义”都有直接的联系。抱打不平一一“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义气”;重友情一一“友情为重”,是“义气”;中和一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是“义气”。因此这三者都是“义气”的不同侧面和层次,也可以说是“义气”的表现形式。反过来推导出来的结论应当是:“义气”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是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部分。横向来看,这三者之间也互相咬合,形成一个圆圈结构。中和是对一切人的,友情楚对朋友的,抱打不平是对敌人的。如果可能,尽量和一切人和平共处,并在—部分人内把中和上升为友情,而在中和形成前或破裂后,为了保护与自己保持中和和友情关系的人,对威胁自己阵营的恶势力,就要抱打不平,从而增加促进友情,并为更大的中和创造条件。这就足它们之间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所说的民族情感,大体是指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对周围世界所做出的情绪反映。其中既有继承的因索,也有生成的成分。《水浒传》中的民族情感,我认为是一方面吸收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影响,又揉进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从而表现出一种从忧世到变世的乐观主义态度。

忧患意识也是中国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庄子·骈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孟子则更明确地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见解,认为不忧世,人就不能生存。但是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又不是厌世和遁世,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凶吉福祸反复思考,从中寻找和发现它们同人的行为之间的联系,进而明确自己的使命。“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和自然合一的伦理要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详、高瞻远囑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经过秦汉两朝的扫荡和压抑,经过魏人的深入探索和蹈厉发扬,它已深沉到我们民族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基本元素。”(高尔太《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西北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水浒传》中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作品中忧患的主体,是以梁山义军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忧患的对象足黑暗的社会,窳败的朝廷。用宋江的话说,是“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谄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史,陷害天下百姓。”(第六十四回)在中央,有高俅、蔡京这样的奸臣和高衙内这样的浮浪子弟;在地方,则有毛太公,西门庆这样的恶霸、地主。他们上下勾结,形成一种无往不在的邪恶势力,把国家搞得乌黑一团,民不聊生。这些忧患对象的存在,对任何一个忧患主体的分子的生存都有一定的威助。这种威胁,不仅仅是可能,而已经是现实。林冲、武松等人都是这种威胁的承担者。在这种威胁面前,那种浩大而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深层心理结构,再一次萌发、启动了。它与人的客观环境、环境与切身利益的因果联系三者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情感状态。对此,人们可以有四种行为选择,来表达这种忧患意识,消除威胁感。一是投身统治者的怀抱,与制造忧患者同流合污。所有的梁山好汉都没有这样做。以“仁”为中心的善恶观和忧患意识交织在一起,使他们本能地站到与忧患制造者对立的一而。卽使一部分人出身于制造忧患的阶级,一旦产生忧患意识,便尽快地告别了这个阶级,走上造反的道路。呼延灼被梁山擒获后,宋江卽以这样的忧患意识劝他入伙:“将军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偏窄之徒:忘人大恩,记人小过。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錢粮,他如何不见你罪责?……”听了这番开导,忧患与责任涌上心头,呼延灼终于决定“愿随鞭镫,决无还理”一一入伙了。二是隐逸山林,或遁入空门。大多数梁山好汉部没有进行这种选择。个别选择这种方式的人也没坚持到底,结果又到了起义军中。如公孙胜隐逸回乡,鲁智深出家瓦棺寺,最终还是发现只有在起义军中,才能实现他们对邪恶势力嫉恶如仇的最佳情感状态。三是依靠外力的作用来改变现实。这一点,书中倒是有过一些反映,如梁山好汉几次祈祷神灵的佑护,九天玄女的赐书以及一些呼风唤雨的战法等。但这些只是作为他们武装斗爭的辅助手段而出现的,不是主要的依靠。四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打击那些邪恶势力。面对使人忧心忡忡的黑暗现实,他们没有灰心,没有丧气,没有逃避,而是那么积极、那么进取,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皇位”,“剪除君侧兇首恶!”“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虽然这些口号也有模糊、矛盾之处,如既然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那为什么还要“忠心报答赵官家”呢?可是,出于对世界的忧患,愿以自己的行为来改变它,这种积极乐观主义的态度,却是一致和明晰的。所谓“乱世出英雄”,说出了英雄治乱的怙绪心理,它也是民族精灵的一部分。
我们在看到《水浒传》民族心理特征的一般特点外,还应注意到它复杂的一面。
第一,民族心理特征与个人心现特征的关系。我们知道,民族是由个人组成,个人是民族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性与个性有共同之处,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个性中属于民族的那部分,就是民族性。而不属于民族性的那呰部分,则或者可能是其它社会属性,如阶级性、靑老年、男女等等;也可能是纯粹的个性,如李逵的莽撞、吴用的机智等。这些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一来前人已多有论及,二来它已非属民族心理,故不在本文论列。
第二,民族心理特征与其它社会属性的关系。民族只是人们对于社会团体划分的一种形式,除此还有多种形式。按阶级可以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按出身可分为市民、艺人、士兵、商人;按年龄可分老年、靑年;按性别可分为男人女人。有的社会心理学家甚至认为二人以上的集体都可称为团体。凡此,毎一种社会团体,都有其共性,如士兵的粗犷、艺人的浪漫,“身体的有力和美是靑年的好处,至于智慧的美则是老年所特有的财产。”(德漠克利特语,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可见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具备几种社会属性,这几种社会属性可以与民族性并存,也可以融合。如李逵和林冲,民族心理特征在他们身上都有体现,但林冲出身高级军官,这种阶级地位使他处事小心,以免地位变化;李逵出身农民无产者,毫无牵挂,所以无所顾忌,这又决定他莽撞的性格。而他们这些个性与其民族心理特征并不矛盾。另外,就每个人来说,民族心理特征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比重也并不平均,如宋江身上“人和”和重友情的性格因素要强一些,鲁智深身上抱打不平的性格要多于他人,等等。
这里还要费几笔来谈谈作品中民族心理与阶级性的关系。诚然,《水浒传》写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也许它还足作品的主题所在。可这并不等于说它就不包括其它社会因素、诸如社会的、心理的、民族的、民俗的、典章制度的等等。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作品,并不意味着对作品中阶级斗争描写的否定,相反,从不同这些角度来研究《水浒传》,可以使我们对作品有更加立体的认识。社会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应决定文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这并非谁排挤谁的问题。如同《韩熙载夜宴图》的音乐史料价值,并不影响人们对作品中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认识一样。
第三,本民族心理特征与其它民族心理特征的关系。我们挖掘和认识某一民族的某些心理特征,并不意味着否定他民族这些心理特征的存在,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特征都是全人类的,”(〔苏〕安德烈耶娃《社会心理学》)只不过各种心理特征的多少和方式不同罢了。如果认为某个民族勤劳,其他民族便都懶惰;某个民族聪穎,其他民族就都是笨蛋,那就有些荒唐。如前面说过的“人和”的心理特征,西方很多哲学家也有过类似的见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美在于和谐,英国夏夫茲博里说:“凡是美的都是和谐和比例适度的。”(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琳娜》、《复活》这几部作品所宣扬的“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爱的宗教”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又是另一民族的另一“人和”心理特征的表现。“托尔斯泰主义”的宗教基础,正如《复活》结尾所引用《福音书》的基督教义“爱仇敌、帮助敌人,为仇敌效劳”等。这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亦是相通的。然而这二种“和”的心理表现的媒介却是不同,《水浒传》的“人和”心理是通过农民起义的现实斗争和失败过程来表现的;而“托尔斯泰主义”则通过作品在表述作者的哲学思想和伦理追求。这又楚中华民族“崇实”和西方人“尙虚”的不同性格所造成的。
从社会心理学和民族学入手,来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对于深入把握作品的内涵,认识民族在某一历史阶段的心理特征和文化传统。从中发现民族精神的发展程度及其优劣成分,促进民族的进步,都是有益的。一个民族若能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剔除其糟粕、发扬光大其精华。那末,这个民族则将永远朝气蓬勃,蒸蒸日上。这也正是笔者意旨所在。

(原载《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二期)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