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
|
2010年2月18日 0:41:02
|
收藏本站 | 设为首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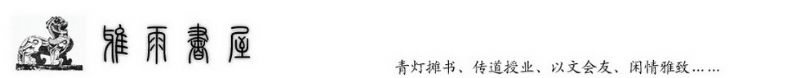
|
|

“雅雨丛谈”
魏晋名士休闲生活中的真性情
——《世说新语》之二十二
宁稼雨
休闲娱乐生活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走向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其已有的娱乐形式往往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二是不断有新的娱乐形式产生。而无论是娱乐形式的发展完善,还是它的创新产生,其动力和起因却往往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思潮的折射。所以某个时代的娱乐生活往往是窥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思潮的重要窗口。从这些娱乐生活的内容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古代传统娱乐形式的变化和发展,而且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娱乐形式的出现。通过这些变化和滋生的内在趋动力的分析,正好可以透视出当时士族文人的精神主潮和文化旋律。
·围棋活动中的个性人格精神

通过对围棋的产生演变到《世说新语》中魏晋文人围棋活动的研究,我们发现,围棋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的出现,经历了一个从社会的道德教化工具发展演变成为个人才能和人格的展现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才会使围棋成为代表个人文化精神修养的形式,跻身于“琴棋书画”四大修养形式之中。
中国是围棋的故乡,其产生时间虽然已难确考,但春秋时期的典籍已有关于围棋的记载。说明它的产生不会晚于春秋。不过将现存早期有关围棋的材料记载与《世说新语》等六朝时期有关围棋活动的材料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到,早期人们对于围棋功能的认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距甚远。早期人们对于围棋功能的认识主要局限在它的教化作用;而从魏晋时期起,士族文人逐渐开始从哲学意味、娱乐功能以至人生态度,也就是广义的精神修养的高度来体会和认识围棋的作用和意义。

因围棋的棋子只有黑白之分,没有等级之别,各子地位平等。刘向《围棋赋》:“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桓谭《新论》:“俗有围棋,或言是兵法之类也。”所以有人认为围棋起源于原始部落会议共同商讨对敌作战的需要,就地画图,用两种不同的小石子代替敌我的兵卒,就双方作战部署进行讨论。这种说法虽然没有实物根据,但比较符合围棋的基本原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疏谓:“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马融《围棋赋》上也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也是从军事角度理解围棋的功用。不过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围棋的就被赋予了浓重的道德教化色彩。在早期的文字记载当中,围棋相传为尧或舜所造。张华《博物志》:“尧造围棋,丹朱善棋。”《广韵》引作:“舜造围棋,丹朱善之。”按丹朱为尧之子,《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博物志》此文正作“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丹朱不得为舜之子,故《广韵》所引有误。但舜造围棋或为另一传说。胡注又云:“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这两种传说尽管主人公不同,但对于围棋功用的介绍却是一样的,即都明确地说出围棋产生于教化的需要。
先秦时期典籍中有关围棋的记载完全可以证实早期围棋的这一道德教化功能。《论语·阳货》:“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于己。”何晏《集解》引马融曰:“为其无所据乐,善生淫欲。”邢昺疏:“《正义》曰:此章疾人之不学也。……言人饱食终日,于善道无所用心,则难以为处矣哉。……夫子为其饱食之之,无所据乐,善生淫欲,故取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戏乎?若其为之,犹胜乎止也。欲令据此为乐则不生淫欲也。”可见孔子是用下围棋的办法来占领那些无所事事的人的时间,以免他们产生淫欲邪念。《孟子·告子》也曾以围棋为喻教育学生:“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对于围棋的这种教化功能的认识直到魏晋时期不仅为正统的儒家人士所继承,而且还有人变本加厉,从礼教角度主张取缔围棋。三国东吴韦曜受太子之令所写下的《博弈论》对围棋发出了严厉的声讨。文中韦曜可谓软硬兼施,或威逼,或诱导,千方百计要使博弈者回心转意,弃旧图新。《晋中兴书》云:“(陶)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奕,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看来韦曜和陶侃的观点比孔子还要过激。孔子尚还能允许人们以下围棋的办法来杜绝滋生淫欲之心,而韦曜和陶侃则干脆要取缔围棋等游戏活动。不过毕竟韦曜在文章中还承认了下围棋所应当具有的智力,承认了凭此智力去猎取功名是不在话下的。而且他们这种观点在当时已经属于主流意识之外的偏狭认识。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失势,人们对于围棋的功能也开始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班固在其《奕旨》中说:

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或虚设豫置,以自卫护,盖象庖牺网罟之制;提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势;一孔有阙,坏颓不振,有似瓠子泛滥之败。作伏设诈,突围横行,田单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赏,苏张之姿。参分有胜而不诛,周文之德;逡巡儒行,保角依旁,却自补续,虽败不亡,缪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这段文字是历史上最早的对围棋棋理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解释的文章。围棋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棋理中所体现的辩证观念、虚实之理、竞争意识,以及心理因素等,在文章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发挥。与孔、孟等儒家人物仅限于对围棋的道德教化作用的认识相比,东汉人对于围棋的认识显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层次和较深的程度。从韦曜和陶侃与班固等人对围棋看法的分歧中似乎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在汉末以来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围棋态度的不同,实际上也是检验一个人思想观念和社会观念上是抱残守旧,固守儒家思想不放,还是扬弃传统,追求新的思想人生观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分水岭和试验剂。
如果说东汉班固等人对于围棋的这种全新认识主要是体现在文字状态的话,那么魏晋文人则更加广泛地将这种对于围棋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的认识运用于生活实践当中。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围棋是士族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和人格修养之一。《世说新语·巧艺》:“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奕余艺莫逮。”可见是否会围棋,是评价一位名士的修养的重要参照。很多名士的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是伴随着高雅神秘的围棋活动而进行的。

他们对于围棋的贪恋已经到了忘我投入的程度。如王导的长子王悦从小就温和乖巧,王导非常疼爱他。每次父子二人下棋,王悦总喜欢按住父亲的手不让动。王导笑着说:“我们还有血缘关系呢,怎么能这样呢?”(见《世说新语·排调》)因大人与初学围棋的儿童棋艺差距很大,可儿童又往往不甘心认输,所以就以不讲理的办法阻止大人行棋。原文中“按指不听”四字,维妙维肖地刻划出王导之子王悦的这一童稚心理和天真之态。而父子二人迷恋围棋之深,也就跃然纸上了。
魏晋名士喜爱围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围棋的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上悟出了名士的人生观念和人格魅力之所在。所以《世说新语·巧艺》谓“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坐在棋桌前的隐居和用手指的清谈可以说是他们对围棋价值魅力的最好理解。沈约曾在《棋品序》中总结围棋的深奥意蕴和汉晋时期人们喜好之状云:“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舍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所以,他们便在忘我的围棋活动中,去体会围棋所蕴含的深奥哲理和文化精神。如一次裴遐在周馥那里做客,这边周馥设宴款待,那边裴遐却和人下起了围棋。周馥手下的司马负责敬酒,裴遐因一心下棋,没有顾得上及时喝酒。那位司马非常恼怒,就把裴遐扯倒在地。裴遐回到座位上,仍然举止如常,面不改色,照旧下棋。事后王衍问他为什么能面不改色?裴遐回答说:“心里想着下棋,也就默默忍受了。”(见《世说新语·雅量》)这种遇事不露声色的气量不仅是当时名士所崇尚的风度雅量,而且也是围棋所倡导的“有胜不诛”,“虽败不亡”的人生态度的表现。梁武帝的《围棋赋》将其形容为“失不为悴,得不为荣”,也正是悟出了这种道理。人所共知的谢安闻淝水大战捷报,不动声色,继续与人对弈(见《世说新语·雅量》);顾邵下围棋时得知儿子夭折,“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见《世说新语·雅量》);甚至孔融的两个儿子听到父亲被捕的消息时,仍然“弈棋端坐不起”(见《世说新语·言语》)等等,都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
既然围棋具有“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人们又如此酷爱围棋,所以这个时期的围棋技艺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其标志之一是围棋的棋盘在这个时期由十七道增为十九道。棋道的增加使围棋增加了难度,也给围棋带来了更大的魅力和刺激。其二是由于人们竞相切磋提高棋艺,并受到九品官人法的影响,魏晋时期开始对棋手的棋艺高低进行分级定品。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于围棋的浓厚兴趣,促使他们跃跃欲试,争取在这咫尺的棋局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个性,以至证明自己的人格尊严。一次丞相王导叫年轻的江虨来和自己下棋。王导的棋艺是比江虨要让两子的水平,可他却想和江虨试试下平子棋的结果会怎样。只见江虨不往棋盘上落子。王导问他原因,江虨说:“恐怕没这个道理吧?”旁边有人说:“这位小伙子的棋艺可是非同寻常啊!”王导慢慢抬起头来说:“我看这位小伙子超过我的,不止是棋艺啊!”(见《世说新语·方正》)从范汪《棋品》可知按照当时的品位划定,王导和江虨有四品之差;而且四品之差的正常差距应当是下让二子棋。但这个故事给予今人的内容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其单纯的史料价值。江虨拒绝和王导下不让子的平子棋(敌道戏),说明他对自己和王导之间的棋艺差距十分清楚,并引以为自豪。在他看来,下了平子棋就等于抹煞了二人的棋艺差距,这不仅是一种乏味的游戏,而且也近乎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而王导对他的赞叹,也正是指这种自强自尊的人格精神。

然而更为动人心弦的,还是他们在围棋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蔑视礼教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阮籍母亲临终时,他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对方见状,便起身告辞。可阮籍却拖住对方不放,“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举号一声,呕血数升,废顿久之”,这才踉踉跄跄地跑回家去(见《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当葬母”条刘注引邓粲《晋纪》)。王坦之在守丧期间,也不顾礼教限制,公然与客人下起围棋(见《世说新语·巧艺》“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条刘注引《语林》)。从表面上看,这或许就是韦曜所批驳的“废事弃业,忘寝与食”,“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但如果明白了当时司马氏政权以推行礼教为名,行党同伐异之实的现实背景的话,就会清楚他们的真实动机并非要亵渎礼教,而是要亵渎那些利用礼教来装扮自己屠刀的人。围棋也就成为一种政治观念角逐的工具了。
围棋从原始时代的作战演示,到先秦时期的教化工具,再到魏晋时期的文人人格和才能的展现,无论是操作规则,还是其文化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巨变的深刻意义,不仅在于它成就和完善了一种代表中华文化的体育文化竞技项目,至今仍风靡世界,而且还在于它对于士族文人的精神文化修养所起到的营造锤炼和积累作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巨变,才会使围棋成为代表文人文化精神修养的重要形式,走进“琴棋书画”之中,走进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走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之中。
·樗蒲活动中的冒险与竞争意识

与古老的围棋相比,樗蒲在汉魏时期要算是新兴的娱乐项目了。虽然相传樗蒲为老子所造,但一般认为这一说法证据不足,难以成立。宋代程大昌《演繁录》认为樗蒲当系由春秋时期的六博发展演变而来。郭双林、肖梅花《中华赌博史》也延续了这一说法。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樗蒲的器具和玩法都与六博有较大的不同,而樗蒲的一些新奇之处往往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有人认为樗蒲传自于西方。其根据是马融《樗蒲赋》中说:“枰则素旃紫罽,出乎西邻。”意谓樗蒲用的用紫色或素色织成的棋盘出自西方邻国。而宋代洪遵《谱双》中讲到的阿拉伯帝国流行的“大食双陆棋”的棋盘也是“以毯为局,织成青地白路”。可知当时西方游牧民族因自然条件限制,多用毛织物作棋盘。其实,可以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一些文字材料。《晋中兴书》载:“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这里虽然还说是老子入胡所作,但已经明确指明樗蒲为“外国戏耳”。又《太平御览》卷七二六引《博物志》言老子入胡造樗蒲时又说:“或云胡人亦为樗蒲卜。”可见樗蒲确实与外国胡人有关。
既然樗蒲与外国胡人有关,那么也就必然带有鲜明的异族文化特征。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钱氏将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一为游牧文化,二为农耕文化,三为商业文化。其中游牧和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为流动的,进取的。……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具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具有鲜明之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故财富有二特征,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樗蒲这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活动,正是体现了西域游牧民族的这一文化精神。马融《樗蒲赋》在形容樗蒲活动的赌博场面及其对于游戏者的心理影响时说:“是以战无常胜,时有逼遂。临敌攘围,事在将帅。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磊落踸踔,并来猥至。先名所射,应声粉溃。胜贵欢悦,负者沉悴。”这种“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的激烈场面和“胜贵欢悦,负者沉悴”的终了效果,与钱穆所概括的游牧文化精神可谓不谋而合。
马融《樗蒲赋》在谈到老子发明樗蒲这种游戏的目的时说:“昔伯阳入戎,以斯消忧。”从他描写的樗蒲活动场面及效果来看,这种带有强烈的刺激感的赌博活动的确可以起到消除忧愁的作用。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种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精神相悖的文化活动如何能够在中国找到合适的生存土壤。从文献记载来看,魏晋时期的正统主流人士显然对樗蒲这一与中国固有文化精神相悖的外来游戏活动持抵制态度。首先,樗蒲这种赌博活动的流行引起了有关人士的警觉和担忧。庾翼曾对下属官员中日益炽烈的樗蒲热忧心忡忡地说:“顷闻诸君有樗蒲过差者。初为是,政事闲暇,以娱乐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渐以成俗。闻之能不怃然?”这种担忧的直接后果就是庾翼等官员公然对樗蒲采取取缔的办法。当庾翼的下属官员参军于瓒上书,陈述樗蒲等嬉戏的危害,并建议“宜一断之“时,庾翼立即批示:“今许其围棋,余悉断!” (见《全晋文》卷三十七)与庾翼类似的还有陶侃。《晋中兴书》记载陶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弈,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在陶侃和庾翼等人看来,所有容易起到涣散人心,有悖儒家入世精神的活动都应在取缔之列,更何况樗蒲这种外国之戏?
然而既然儒家的正统人士连儒家思想本身在汉魏时期的颓势都无法挽救,那么他们对于樗蒲等有悖儒家教化精神的游戏活动的禁止,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樗蒲能够在魏晋时期广泛流行,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随着儒家思想的衰微,以往社会对于个人那过多的束缚和责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和逆反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反礼法之士的行为选择是唯与儒家思想观念相悖为是从。所有儒家思想反对和禁止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新潮而大加提倡。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到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也”,再到整个魏晋时期士族名士的种种放诞举止,都是作为儒家思想观念的反动的产物。东晋时期的葛洪曾以极大的愤慨,来谴责这种在儒家正统观念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汉之末世,……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以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訚訚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业。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见《抱朴子·疾谬》)又说:“闻之汉末诸无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骄慢傲,不入道检者,为都魁雄伯、四通八达,皆背叛礼教而从事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弊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见《抱朴子·刺骄》)葛洪的话不无偏激,但却大体上反映出当世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土崩瓦解的真实情况。
受惯了儒家思想循规蹈矩的观念教诲的人,一旦抛掉头上的紧箍咒,便以极大的自由精神去寻求一些越轨后的快感。而樗蒲这种外来的赌博游戏恰恰可以满足他们的这种心理。作为士族名士的教科书,《世说新语》收录了许多名士以樗蒲活动展示其个性魅力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有关樗蒲活动记载的珍贵史料,而且也有助于认识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由于樗蒲活动带有赌博的性质,输赢的筹码很大,甚至顷刻间可以使人倾家荡产,所以它吸引了许多寻求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弄潮儿。如温峤官位不高时,屡次和扬州、淮中的客商樗蒱赌博,总是输给别人。一次樗蒱输了很多钱无法还债,被人扣为人质。他在船上看见好朋友庾亮,就大喊庾亮来赎救自己。庾亮把钱送过去,他才被赎出来。类似的事情有过多次(见《世说新语·任诞》)。尽管是屡战屡败,却还要屡败屡战。这股不服输的劲头儿来自樗蒲活动尽管可能,却十分渺茫的胜利的机会。然而樗蒲的魅力也就在于通过对参与者这股冒险和竞争意识的调动。

由于这种魅力的吸引,有些乐此不疲者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如《世说新语·任诞》载桓温年轻时家境贫穷,樗蒱又输得很厉害,债主逼催赌债很急。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解救的办法。有个叫袁耽的人为人豪爽而又很有才能,桓温就想向他求助。可袁耽当时正在守孝,桓温怕让对方为难,就委婉试探着把自己的意思说了。没想到袁耽答应得非常痛快,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为难。于是马上就换去孝服,把头上的布孝帽随手揣在怀里,告诉桓温自己会大获全胜,要桓温在旁呐喊助威,然后就跟桓温走,去和债主樗蒱。袁耽的樗蒱技艺向来有名,债主上场之后说:“你该不会把袁彦道(耽)搬来吧?”于是就开始樗蒱。每次都下十万钱的赌注,一直上升到一百万钱一注。只见袁耽投掷筹码的时候高声呼叫,旁若无人。桓温也在一旁应声附和,只见袁耽所投,都是“卢”、“稚”之类的赢彩。顷刻之间,债主就输了数百万。这时袁耽从怀里掏出布孝帽扔向债主说:“认识袁彦道(耽)吗?”这篇故事可谓是马融《樗蒲赋》所描绘的“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先名所射,应声粉溃。胜贵欢悦,负者沉悴”的激烈刺激场面。文中袁耽能够放下父母的守孝而去替桓温出气报仇,其动力既不是哥们儿意气,也不是挣钱的欲望,他只是想在樗蒲游戏中一展才华,证明自己的超人能力和不可替代的价值。西域游牧文化的冒险竞争意识对中原士人的影响,魏晋士人将个人的价值置于礼教礼法之上,于此可见一斑。从中亦可见习樗蒲者在性格和人格方面所形成的自信和自尊。又如王献之孩童时曾观看家里的一些门生樗蒱,见到其中有强有弱,,就说:“南风不竞。”门生轻视他是个小孩,就说:“这位小家伙也算是管中窥豹,有时也能可见一斑啊!”王献之气得瞪大眼睛说:“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言外之意就是根本没把你们这些人放在眼里。“南风不竞”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意谓南边一方要输。说明王献之虽然年少,樗蒲水平已经不低。“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一句当承续上句,意谓与荀粲和刘惔相比,我或许可称“管中窥豹”,但与你们这些平庸之辈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以此表现王献之在樗蒲能力乃至人格上的充分自信。
正因为樗蒲能够充分体现出参与者的性格和人格,所以人们常以此来评价品骘人物。一次桓温和袁耽樗蒱,袁耽掷出的骰子不理想,就满脸怒气地扔掉了五木。温峤听说后说:“见到袁耽迁怒于五木,才知道当年的颜回是多么值得尊敬。”(见《世说新语·忿狷》)从上引故事已经看出,袁耽是视樗蒲比祖宗都要重要的人,所以难以忍受樗蒲失败的痛苦,直抒胸臆。这在温文尔雅的儒家观念看来,是有失体统的。有意思的是,那个责怪他迁怒失态的温峤,本人也曾是屡败屡战的樗蒲迷,却要对袁耽指手划脚。这种评价正好从反面看出袁耽在樗蒲活动中对儒家人格规范的叛逆。又有人从樗蒲活动中去观察和分析一个人的政治处世习惯,如桓温将要征伐蜀地的时候,各位居官当权的贤士都认为李势盘踞蜀地已久,承袭基业也有好几代,而且又占据长江上游的天时之利,三峡地区也不能轻易攻克。只有刘惔持不同意见:“他一定能攻克蜀地。从他樗蒱的作为中就可以看出,没有把握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做的。”(见《世说新语·识鉴》)此事在永和二年(346)。其实当时李势成汉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不堪一击。桓温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决然进兵的。而刘惔对战局必胜的预见,却是通过桓温平常樗蒲时不作无把握之事的习惯而看出的。可见樗蒲活动已经与人们的政治生活发生联系了。又如一次王敦和手下的参军樗蒱,参军的局面上已经五马领头,就要胜利在望的时候,突然五马被杀。参军感慨地说:“周家世代名望,然而却没有位至三公的人。周顗功亏一篑,好似下官的五马领头。”王敦慨然流涕说:“周顗小时候和我在东宫相遇,我们一见如故,他当时就发誓要位至三司。没想到不幸被王法所杀。真是令人痛心不已啊!”(见《世说新语·尤悔》)及刘孝标注)“五马领头而不克”即是以樗蒲为喻,说周顗已经胜局在握,如同樗蒲中的五马领头,但终于功败垂成。《晋纪》中王敦参军也是以樗蒲为喻,说周顗即将成都时功亏一篑,马头被杀。可见故事中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樗蒲活动为喻,影射人们的政治命运。则可见人们已经从樗蒲活动的胜败难料中,看到它与官场政治命运顷刻风云突变的相似之处。说明他们对樗蒲活动冒险和竞争精神的向往,仍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官本位的本体樊笼。
可见樗蒲这一外来的竞技游戏形式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的流行,成为体现魏晋士族文人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的重要媒介。在儒家思想势颓,老庄无为自由精神盛行的魏晋时期,樗蒲活动中原有的体现西域民族冒险精神的内涵与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充分表现出魏晋士人追求刺激冒险、追求个性自尊、自由和放达任性的人格精神。从而体现出任何具体的文化娱乐形式都要受到时代文化总体精神制约这一文化史、社会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弹棋活动中的消遣娱乐情趣
与围棋和樗蒲活动相比,弹棋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既不是先秦古代游戏的延续,也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从汉魏时期在中国本土兴起的娱乐游戏方式;二是它没有受到礼教政治等社会因素的制约,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消遣娱乐活动。

关于弹棋的起源,有三种说法。一是汉武帝时东方朔说。《弹棋经序》言汉武帝喜好蹴鞠之戏,群臣谏而不止。东方朔便以弹棋之戏进献武帝。武帝得此戏便舍蹴鞠而好弹棋了;二是汉成帝时刘向说。《弹棋赋叙》谓汉成帝好蹴鞠,刘向认为蹴鞠“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而作弹棋”;三是魏宫妆奁说。《世说新语·巧艺》:“弹棋始自魏宫内用妆奁戏。”但此说明显站不住脚。刘孝标注在引述傅玄《弹棋经叙》所云成帝时刘向造弹棋事后又言:“按玄此言,则弹棋之戏其来久矣。且《梁冀传》云:‘冀善弹棋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谬矣。”所谓魏宫妆奁说实际上是指弹棋在汉末魏初一度断绝后再度兴起的情况而言。《弹棋经后序》云:“自后汉冲、质已后,此艺中绝。至献帝建安中,曹公执政,禁阑幽密,至于博弈之具,皆不得妄置宫中。宫人因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即取类于弹棋也。及魏文帝受禅,因宫人所为更习弹棋焉。”观此可知弹棋何以在魏宫复兴,何以称用妆奁戏之说。至于武帝成帝二说虽已无法确定,然因其时间都在汉代,其起因也完全相同,故实际上二说为一说两传而已。
从弹棋的起源可以看到,它是一种模仿蹴鞠活动而设计的一种棋类活动。经过重新设计的弹棋,避免了蹴鞠活动的强体力活动,突出了智力因素和技巧的作用,所以也就增强了它的文化品位和消遣娱乐功能,带上了道家神仙色彩。《弹棋经序》云:“弹棋者,仙家之戏也。”《弹棋经后序》也说:“弹棋者,雅戏也。非同乎五白枭橛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固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盖道家所为,欲习其偃亚导引之法,击博腾掷之妙,自畅耳。”可见它所吸引人们入迷的,不像围棋那样需要用诡计欺骗对方,也不像樗蒲那样紧张刺激。它将所有棋子都摆在棋盘上,在双方共同的视线中进行智力和技巧的较量。从而体现出道家清净无为,淡薄自然的价值取向。所以在老庄思想盛行,出世之想日炽的魏晋时期,尤为人青睐。经过曹丕的提倡,弹棋又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弹棋经后序》称:“当时朝臣名士,无不争能。故帝与吴季量(当作‘重’)书曰:‘弹棋,间设者也。’”曹丕本人就是一位弹棋妙手,他自己在《典论》中说到自己少年时候就喜欢各种游戏,尤其对弹棋略尽其妙。据《世说新语·巧艺》,魏文帝曹丕玩弹棋特别精妙,能用毛巾角轻击棋子,百发百中。有位客人自称也很会玩,曹丕就让他试试。客人戴着葛布头巾,低下头用头巾角去拨击棋子,其巧妙胜过了文帝曹丕。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人们在弹棋活动中确实是看重玩者的技巧。按照一般的弹棋玩法,双方将自己的棋子摆好后,要用手来弹拨棋子,使之穿过棋盘中间的隆起部分,射入对方的圆洞,有似足球的射门。用手弹拨已属不易,而曹丕却高人一筹,能够用手巾角拂动棋子,达到别人用手才能实现的目的;而更为高妙的是那位客人,他竟然能够用戴在头上的葛角巾,用脑袋的晃动来使葛巾角将棋子扫进对方圆洞。可谓强中更有强中手。在这已经近乎杂技的弹棋活动中,可以看出人们如何以技巧的竞争为手段,进而达到消遣和娱乐的目的。至两晋南北朝间,弹棋活动更为普及。葛洪《抱扑子·疾谬》:“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樗蒲、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繻纨绔之侧。”葛洪的看法不免偏激,但当时弹棋的流行却确如他所描绘。一次刘惔在盛暑时去拜访王导,只见王导把弹棋盘放在肚皮上纳凉,嘴里惬意地说:“何乃渹(吴语凉快意)!”王导以吴语与刘惔应答,倒是他另有用意。然而他在盛暑之月,将弹棋棋盘放在肚子上纳凉的办法,却从侧面告诉我们那是他时刻放在手边,随时可以取来游戏玩耍的娱乐工具。弹棋活动之盛行,于此可见一斑。宋文帝刘义隆曾将当时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和徐道度医术并称天下“五绝”(见《南史·徐文伯传》)。可知至南北朝时弹棋已经十分盛行。
弹棋游戏的消遣和娱乐的功能,从总体的观念上与魏晋时期的围棋和樗蒲是一致的。这就是不再从主观上去服从和追求从社会礼法角度强调这些游戏的功利目的,而且强调游戏娱乐活动本身的消遣性和娱乐性。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中说:“弹棋亦近世雅戏,消愁解愦,时可为之。”已经说明人们对这些娱乐游戏活动的消遣娱乐功能的认可。与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对围棋活动教化作用的规定,人们的娱乐观念应当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弹棋活动从其肇始发轫,就以脱离礼法规范束缚的纯粹娱乐面目出现,可以说是这种纯娱乐观念比较成熟的标志。


(本文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2023年第一期,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版)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