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
|
2010年2月18日 0:41:02
|
收藏本站 | 设为首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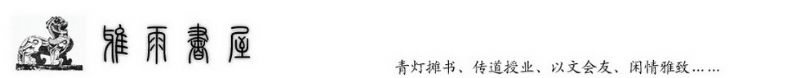
|
|

(续前)
“道统”与“势统”关系的核心和本质,是“真理”和“权力”的各自社会价值如何平衡的问题。士人是“道统”的主要承载者和代言人,皇权是“势统”代表者和掌控方。二者是相互抵牾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从依存角度看,权力一方需要有真理的肯定和认可,以取代执行权力的合法性;真理一方也需要有权力的认可和工作保障。从抵牾的角度看,双方的和谐稳定关系需要一个能够维持平衡的基点。一旦失去平衡,就会产生矛盾对立,激化社会矛盾。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有待于双方的配合和合作,共同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真理与权力关系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于一个国家政权结构和政治制度的成熟,另一方面则有赖于一个知识阶层群体的形成和成熟。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应该就是西周时期了,从那时起,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真理和权力伴随咬合和拒斥的滚动历史帷幕。
余英时先生曾将东西方真理与权力之间关系状况做过一个对比,二者都经历过一个真理代言人与权力操控者之间边界范围和职能属性从模糊到分离清晰的过程。但分离之后的状况不尽相同。在西方,教会和政府形成两个分别代表所谓真理道义和权力掌控的部门。二者不但泾渭分明,而且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更大的社会权威性。可是中国的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代表真理一方的士人阶层始终没有能够像西方教会那样取得与政权分庭抗礼,甚至凌驾其上的地位。[①]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难以撼动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两个方面。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血缘关系社会走向地缘关系社会。而中国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血缘关系和血缘意识未能实现充分解体,以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血缘观念意识还以各种形式和途径顽固延续。无论是国家层面同一朝代皇位继承,还是社会大众层面家庭财产继承,依然严格按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始血缘关系为根据和常理,从而形成根深蒂固的家族血缘宗法观念意识。血缘宗法观念不仅表现在权力和财产继承方面,还广泛深入影响到国家社会管理方面。其结果就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核心就是权力大于一切,唯我独尊观念为天经地义之法则。处在如此背景下的真理与权力关系,为真理代言的难度也就不言而喻了。“道统”与“势统”也就难以形成和谐与良性的互动关系。
西周时期是中国完全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从“道统”与“势统”的关系来看,虽然双方各自已经进入成熟的状态,但就相互之间的影响作用力度来看,“道统”一方完全在“势统”的笼罩统驭之下。“学在官府”已经从社会制度上规定了作为真理载体的知识和学术只能受“势统”一方的管理掌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从个人的社会身份上规定了包括真理代言人的文人必须对“势统”一方俯首称臣。
春秋战国的动荡局势,激荡出“道统”“势统”关系态势的新格局,也为为真理代言的“道统”一方有了清晰的社会群体形象和职业特征。首先是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打破,使得原先那些吃官饭的文化人失业走向社会,成为职业自由人。他们开始把手里的知识作为谋生的手段,大胆思想,碰撞出“百家争鸣”的灿烂思想文化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道统”一方最为风光体面的时段。作为真理和知识代言人,他们不仅全面打造创立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而且同时在总体上也得到“势统”一方的认可与支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道统”与“势统”关系相对和谐而且堪称双赢的时代。所谓“双赢”是指双方在此期间各自均有所得。就“道统”一方来说,他们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获得人身自由的基础上,也获得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去周游列国,去朝秦暮楚,去合纵连横,去发表各种完全对立的各种思想观点,从而创造社会价值;就“势统”一方来说,他们最大的收获在于,无论“道统”们怎样变换行为方式,怎样“百家争鸣”,最可放心的只有一点:他们所有的行为和思想,都集中汇合在“君人南面之术”,即“为我所用”这个主线上。“势统”用还给士人自由人身和自由言论的代价,换来了“道统”一方全方位的支持和配合。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道统”与“势统”相处最良性,对中国历史和人类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进入秦汉,随着秦始皇的一把烈火,“道统”与“势统”之间即可进入势同水火的敌对状态。嗣后,汉代“势统”执政理念的变换,“道统”与“势统”的和谐良性关系开始进入倒退趋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决策的推行,意味着持非儒家思想观点的人只能闭嘴不能说话了。这显然是对战国时期自由和谐局面的背离和逆反。这样的政策必然导致言论“一言堂”的局面,也影响到很多士人的行为方式和处世态度。像东方朔这样生活在汉武帝身边的人,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对汉武帝的为政为人发挥一些制约和影响作用[②],比如很多野史杂记里提到他每每“谲谏”成功的故事。这些谲谏行为往往通过讽谏的方式对刘彻进行监督和批评引导,某种意义上具有代表真理的“道统”监督批评“势统”的作用。看上去似乎已经是高高在上,而且能够发挥真理代言人作用了,但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他在汉武帝那里不过是“用之者则如虎,不用者则如鼠”,他自己过的日子也只能是“伴君如伴虎”的惨状。另外像贾谊和司马相如,看上去似乎也能深得文帝和武帝赏识重用。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他们与帝王之间关系似乎还不能上升到“道统”与“势统”关系的层面上去理解和认知。真正能够从“道统”与“势统”层面对士人和皇权之间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东汉以后“势统”一方将儒家伦理道德政治化,绑架包括士人在内的整个社会,从而限制士人的思想创新和行为自由。东汉时期为博得“孝子”美誉沽名钓誉者层出不穷,正是“势统”这个导向的恶劣后果。与此同时,皇权内部矛盾重重,宦官与外戚矛盾激化,殃及国家,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终于酿成清议运动和党锢之祸。清议运动和党锢之祸标志着汉代“道统”一方为真理代言的努力遭到“势统”一方的残酷镇压。战国以来“道统”与“势统”的和谐良性关系,完全遭到解体,二者关系从此进入黑暗时代。
这样的社会背景给魏晋士人的“道统”责任担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是,真理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魏晋士人也就没有辜负时代赋予他们的“道统”责任与良知诉求。他们通过不同途径,以多种方式渠道履行作为“道统”一方对“势统”的监督责任和批评义务。
首先是明确以“势统”批判者的面目出现来指斥批评“势统”各种不当行为,并公开与之。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孔融和祢衡。从进入东汉朝廷上层臣僚班子开始,孔融就一直以一位社会批判者的姿态来指点江山,评骘世事。他先是反对朝廷打算礼葬不光彩窝囊而死的太傅马日磾的计划,继而又极力否定推翻朝廷恢复肉刑的计划,然后又反对献帝打算为几位夭折王室举行四时祭祀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孔融的社会批判者的形象逐渐明确清晰起来。如果说孔融对汉献帝的批评还算温和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疾之如仇的曹操的批判则是酣畅淋漓,嬉笑怒骂,毫无保留。他先是竭力反对曹操终生引以为豪的东征乌丸计划,继而又几次就禁酒问题与曹操展开激烈辩论。更有甚者,他甚至在曹操父子争夺甄氏的事情上把曹操狠狠恶搞了一通[③],以至为自己埋下了送命之祸。与孔融相比,祢衡对曹操的态度就更加直接和暴躁。本来是孔融向曹操极力推荐祢衡,而且对祢衡赞美有加。曹操本来就爱才,听说后几次要约祢衡见面。不想祢衡不但不见面,反而四处散步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舆论。曹操听说后震怒,但如果直接惩治,又显得有失风度。于是便打算安排祢衡去做击鼓手来羞辱他。可是曹操万万没有想到,却被祢衡以裸体击鼓方式羞辱了自己一番[④]。孔融和祢衡最后都因此遭遇不幸,这个的现象说明清议运动遭遇镇压后,广大士人对于“势统”的抵触对立心态,昭示“道统”与“势统”关系破裂之后的对抗对立状态。
其次是清醒意识到自己“道统”身份与“势统”距离,主动与之保持疏离和不合作距离感。“道统”“势统”之间关系的复杂微妙之处还在于,作为执政者的“势统”方面,手里掌握着能够决定“道统”方面承担者利益资源乃至身家性命的权力。如果仅从利益角度考虑,士人和社会其他人等都需要与执政的“势统”一方搞好关系,以避免利益损失。但真理和良知之所以没有彻底泯灭,就是因为在任何时代,总有那么一些有识之士,明明知道某些行为会产生不利于自己利益的负面作用,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真理代言人的“道统”身份,主动与他们认为已经“无道”的“势统”一方划清保持界限。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嵇康和阮籍。
无论是从家庭社会背景,还是个人条件角度考量,嵇康都有可能成为魏晋时期官场上炙手可热的天花板级人物。可他却偏偏没有走上这条光明大道。他在经历曹魏政权和司马氏政权之后,清醒而深刻认识到,他们经营努力的目标,都不是什么国家社稷,而是一己私利,因而完全断绝了对于功利名教利益的留恋与追求。当他的老友山涛推荐他入朝做官时,他借题发挥,以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表达自己与司马氏政权的不合作态度。表面上看,他所给出不能接受山涛举荐就任的理由,主要是自己个人秉性原因(像必不可堪者七,甚不可堪者二),但实际上通过这些陈述,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与司马氏政权的对立立场和不合作态度。因为他已经公开表明他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倾向,而“汤武”“周孔”正是司马氏政权借以维护所谓名教统治的主干凭据。这个势不两立的态势也正是当时“道统”与“势统”分庭抗礼局面的形象写照。
阮籍虽然没有像嵇康那样和盘托出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他们俩堪称是同道加兄弟,只是个人秉性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首先,对于以“汤武”“周孔”为中心的名教礼教,阮籍和嵇康同样明确持反对态度。他不仅在言论上公开提出“无君论”的观点,而且在行动上每每冒犯礼教。礼教明确规定“男女授受不亲”,甚至具体到“叔嫂不通问”的程度。可阮籍却偏偏专与嫂子聊天,而且还公然声称:“礼岂为我辈设也!”母亲去世,阮籍不仅公然违背礼教规定,喝酒吃肉,而且连友人前来吊唁,阮籍也不按礼教程序进行接待[⑤]。其次,阮籍本人与司马昭本人关系有些微妙。他曾受人邀请,大醉为司马昭写过劝进表,并且也的确因此得到过司马昭的保护。但因此事并非阮籍本心所愿,所以引以为耻,懊悔痛苦。能够证明他这片苦心的是他严守与司马氏政权关系的底线,为拒绝与司马氏联姻,他曾大醉60天,不给司马昭提亲的机会。他谋职步兵校尉,也并非有修齐治平的大志,而是奔着办公室壁橱中的好酒而去[⑥]。可见他灵魂深处以“道统”自任,与“势统”保持距离的明确认知。
再次是“道统”参与和取代“势统”的尝试。魏晋以降,随着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崛起,这个社会群体很快产生政治到文化的各种利益诉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成功实现门阀士族取代皇权成为国家政权主要决策势力。除了门阀士族自身的实力强大外,从社会环境来看,西晋王朝覆亡,使皇权遭到重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皇权借助门阀士族力量,举朝南迁,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东晋王朝的重要政治特点,就是门阀士族参与朝政,左右朝政的门阀政治。因为门阀士族的主体也是魏晋士人阶层的主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门阀士族参与东晋王朝政治,既是西周之后“道统”与“势统”的再度握手联合,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道势关系中“道统”居于主导地位的罕见局面[⑦]。王导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的经历,既是这场历史剧的开始,也是这场剧目后来的范本:
时元帝为琅琊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邪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现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讲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义。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晋书·王导传》)[⑧]
文中可见,东晋王朝始建过程中,王导完全是总导演的身份,从晋元帝到朝臣和吴中大族,均在王导策划安排下各司其职,各就各位,引导东晋王朝逐渐步入正轨。以“道统”身份参与并左右朝政的王导,不仅以政治家的能力辅佐稳定局面,而且还充分发挥“道统”传人的思想和智慧优势,在执政理念,文化学术传承等各个方面去努力实践“道统”一方在获得自由活动空间后尽最大可能实现其社会价值,并与“势统”一方一起再次谱写一曲双方良性合作的和谐凯歌。
综上可见,魏晋时期从“道势”之间的分离开始,经过碰撞磨合,终于回到良性和谐状态。这一状态回归不仅是对西周双方和谐局面的继承,同时,也为嗣后唐代科举制度成为平衡“道统”“势统”新和谐局面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坚实的基础。
以上三个方面如果上升到人生态度的层面,应该就是汉代以来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被魏晋士人的审美人生态度所取代。按照一般知识理解,人生态度属于人生观的范畴,而人生观又从属于世界观。所以,人生态度是决定个人生活道路的方向选择,价值利益取舍,生活美丑判断等等重要人生大问题。
人生态度基本可以分为功利型和超脱审美型。朱光潜先生说过,人生好比是一出戏剧,“世间人有生来是演戏的,也有生来是看戏的。这演与看的分别主要地在如何安顿自我上面见出。演戏要置身局中,时时把‘我’抬出来,使我成为推动机器的枢纽,在这世界中产生变化,就在这产生变化上实现自我;看戏要置身局外,时时把‘我’搁在旁边,始终维持一个观照者的地位,吸纳这世界中的一切变化,使它们在眼中成为可欣赏的图画,就在这变化图画的欣赏上面实现自我。因为有这个区别,演戏要热要动,看戏要冷要静。”[⑨]所谓看戏和演戏,也正是功利型和超脱审美型两种人生态度的同义表述。如果从中国传统处世思想角度看,也就是儒家入世思想和道家出世思想在人生态度方面的影响和反映。
从这个角度切入可以发现,从汉代推重儒家思想以来,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影响并构建出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为核心的入世人生态度,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为国家和社会建言献策成为很多文人的热衷与追求。他们或“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途”(司马相如《上林赋》),或“经纶训典,赋纳以言”(张衡《南都赋》)。不仅如此,他们还往往直接用经义内容去表达其入世理念和态度: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 (班固《两都赋》)[⑩]
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入世者的宏伟蓝图和美好理想。但在入世思想的强大惯性作用下,即便在入世人生道路上碰壁后的牢骚,或是忧虑,其实也同样是入世精神的折射和反映。汉代一批以失意经历为背景而生发的“不遇”主题,便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像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司马相如《美人赋》、刘歆《遂初赋》、班固《幽通赋》,以及董仲舒《士不遇赋》等,都是他们在仕途上未能获得重用而产生的不平以及无可奈何的感伤。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汉代人那种昂扬向上的激情逐渐淡化,超凡脱俗道家出世色彩的人生态度逐渐演变为士人主流心态。
促成魏晋士人人生态度发生逆转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巨变,尤其是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主角的现实。汉代国势强大,百业繁荣,为士人展示提供了入世人生的广阔舞台,但东汉以后,战乱频仍,人命危浅,国势衰败,人们所见,不再是一个可以大展宏图,大有作为的可入之世。以往儒家入世之心因此受到压抑,也是势在必然。与此同时,随着门阀士族的崛起,以往以儒家孝悌礼教为核心,以举贤良方正为程序渠道的人才选拔机制已经被“九品中正制”保护下以家族背景为依据的人才进取途径所取代。这意味着,对于门阀士族来说,积极用世入世,不再是唯一的人生进取发展出口;对于一般寒族庶族来说,没有家族背景,也很难实现入世,在此背景下,经济实力雄厚并已逐渐获得政治权力的门阀士族文人,逐渐开始把以往帝王文化的政治核心转向文化核心。其中首要条件就是把以往服务于帝王文化的功利入世人生态度转化为施展实现士族文人精神世界的审美人生态度。这一重要的文人心态变化不仅影响到魏晋士人文化格局构建,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后来唐宋时期士人文化高潮的到来。
由实用功利人生态度转向审美人生态度的关键是价值取向的变化。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就已经通过那个著名大树故事阐发了这个重要的人生哲理: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11]
同样一棵樗树,如果从实用功利角度看,它毫无用处;而从审美角度看,把它放在广袤的原野中,使其获得自由生长,无论是它自己,还是它的观众,都是一件美好惬意的事情。庄子这里意在昭示一种摈弃实用功利生活态度的价值观念,也就是自由审美的人生态度。然而这种美好的人生态度在汉代入世精神笼罩下,基本湮灭无闻了。是魏晋士人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重新开始考虑一种告别功利实用的审美人生态度: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世说新语·言语》)[12]
这个故事已经明确看出,在实用功利和审美超脱两种截然对立的人生态度中,后者显然居于优选地位。正因为有如此明确的审美人生态度,才使得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审美韵味,并且多方面展示出人生审美的高超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
表现之一是善于在静观生活中发现生活之美。生活之美本来无处不在,发现它对任何人也是机会均等的。但之所以不是人人都能发现生活之美,原因就在于碌碌世事分散了人们的观察注意力,而功利实用的观念又遮住了人们的审美目光。所以美只能属于能够发现它的人。正如罗丹所说:“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13]告别汉代功利实用人生态度的魏晋士人也正是如此。晋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14]书圣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共登冶城,谢安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15]。那位披着袈裟的名士支遁喜爱养马,人言“道人畜马不韵”,支答曰:“贫道重其神骏。”[16]支遁不仅在骏马奔驰中体味出人生自由的意义,而且推而广之,在其他动物行动中去寻找人生之美:
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新语·言语》)[17]
可见他们长于观照生活,善于从审美的高度上把握和玩味生活。华林园与冶城的风景,骏马与仙鹤的风姿,都是他们审美人生的得意佳作。
表现之二是善于把自己打造成为人生艺术品实现自我塑造与欣赏。人生如戏,如同戏剧理论界三种不同的经典表演理论体系阐释,人生演戏的舞台上也有不同的表演套路和体系特色。儒家入世精神的人生表演,如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理念,演员需要与角色融为一体,完全进入角色,把观众视为现实生活的“第四堵墙”,也就是要忘记自己的表演身份。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种入世表演的总结概括。而受到老庄自由人生精神影响的魏晋士人,其人生表演与要求演员与角色明确而清晰地保持距离,如同中国戏曲表演的程式化和德国布莱希特表演理论的“间离效果”。这有些接近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也就是表演者能够清醒认识到自己是以游戏的态度,来扮演人生的角色。不但能演给人看,还能自我欣赏。在儒家统领的功利性生活信条规范下,人们只能按照“不逾矩”的规矩来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社会利益和资源,那也就只能与生活的审美感受失之交臂。进入魏晋,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功利型活法的无趣和可怜,便明确主张告别限制束缚,解放自己,寻找自由人生。嵇康自称:
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与山巨源绝交书》)[18]
这里描述的人物行为方式与儒家入世范式完全背道而驰,它堪称追求自由人生的宣言书。作者明确把生命本性作为最宝贵的东西来确定,来坚持,并且因为有同伴的认可和老庄思想的滋养而愈加自信和坚定。这是一种由行为者本人描绘塑造的自我自由行为画像。有了这样的思想根基,便可以自由地去设计和实践自己的人生: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世说新语·任诞》)[19]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20]
如果了解到此前儒家入世功利人生的模板和面具式的生活样貌,也就不难理解和赞许:这貌似放诞颓废的行为方式,既包含对功利人生的彻底颠覆,更是充分表达了自由人生的信念和激情。而这种放诞玩笑人生态度还有其内在的深刻意义,这就是在超越现实生活基础上对于自我的完全实现——把自我的行为方式视为一件艺术品向社会展示,并自我欣赏。庄子强调张扬的“身与物化”“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两冥的人生境界在魏晋士人这里得到充分实现和高蹈。他们努力把自己按照艺术化、审美化的方向践行,去实现庄子倡导的那个理想境界。王忱慨叹:“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21]王荟声称:“酒自引人著胜地。”[22]以饮酒为媒介,希望进入形神相亲的“胜地”,便是那个物我两冥的境界。“而在激情高涨时,主体便隐失于完全的自身遗忘状态”[23]。这些放诞行为背后隐含着这些人生艺术家的内心独白:我的人生乐趣和追求,就是来源于欣赏这些我自己创造的艺术品。你们不理解吗?那么好,连同这些不理解,一起成为我审美观照的对象吧!这里,魏晋士人以狂放的举止来扮演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生戏剧,以身躯为彩笔,来描绘人生的苦乐图画,“人不再是艺术家,人变成了艺术品;在这里,在醉的战栗中,整个自然的艺术强力得到了彰显,臻至“太一”最高的狂喜满足。人这种最高贵的陶土,这种最可珍爱的大理石,在这里得到捏制和雕琢,而向着狄奥尼索斯的宇宙艺术家的雕琢之声,响起厄琉西斯的秘仪呼声:‘万民啊,你们倒下来了?宇宙啊,你能预感到那些造物主吗?’”[24]
表现之三是与生活保持有距离审美。无论是静观中发现生活之美,还是审美角度的自我形象塑造,都需要把握好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本来这个视角来自于美学和艺术理论角度。瑞士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审美需要距离的学说,主要是指艺术品的欣赏[25]。但他论证这个观点所举出的著名“雾海行船”例子,却是一个富有画面感的生活场景。正是这个富有说服力的生动事例,让我们联想到与之具有惊人相似之处的魏晋士人生活故事: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世说新语·雅量》)[26]
船上对于遇到风浪的两种态度,也正是实用功利和审美生活的两种截然对立态度。从实用功利角度看,风急浪涌,有生命危险;而从审美角度看,惊涛骇浪,波澜壮阔,乃是难得的美丽图景。文中观众及作者对于谢安行为的赞许推重,反映了那个时代以审美人生态度取代功利实用人生态度的完胜。于是,对生活有距离的审美便大行其道: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27]
功利实用人生态度注重事情结果,凡事需有始有终,结果才是事情的价值所在。而在审美人生态度那里,结果被完全忽略了。它关注重视的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兴之所至过程本身。“兴”是一切活动过程中的审美愉悦,它才是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与庸庸碌碌的功利实用结果相比,“兴”才是王者。儒家礼教名教那套蝇营狗苟的功利结果,已经被“兴”荡涤冲刷得无处藏身,无颜面世。魏晋士人的审美人生态度,也成为历代文人心中向往暗恋的美好人生境界。
综上可见,魏晋文化总体潮流精神包括物质与精神,个体与社会,“道统”与“势统”,审美与功利四个方面。其外在表现是士人社会行为等现象方面,但折射的内在核心要点是士人人格独立精神。它通过这些渠道全面构建了中国士人文化以“道优于器”传统思想为基础的精神文化体系,并在士人人格社会实践方面得到认定和落实;它不仅明确夯实了中国古代士人文化的基本底色和价值取向,而且也为魏晋之后唐宋士人文化高潮繁荣局面的到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文化潮流引领作用。
[①] 参见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比如一些野史笔记中提到他每每“谲谏”成功的传闻故事,见《汉武帝内传》等。
[③] 《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五官将纳熙妻也,孔融与太祖书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博学,真谓书传所记。后见融问之,对日:‘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④] 见《世说新语·言语》“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条及该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⑤] 均见《世说新语··任诞》。
[⑥] 见《世说新语·任诞》。
[⑦] 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⑧] 房玄龄等《晋书·王导传》,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排印本,第2745-2746页。
[⑨] 《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50页。
[⑩] 班固《东都赋》,萧统编《文选》卷一,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第31页。
[11]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诸子集成》1954年,第20-21页。
[12]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140-141页。
[13] 罗丹口述,葛赛尔记,沈琪译,吴作人校,《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
[14]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121页。
[15] 见《世说新语·言语》。
[16] 见《世说新语·言语》。
[17]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页。
[18]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萧统编《文选》卷四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第601页。
[19] 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731页。
[20] 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740页。
[21] 见《世说新语·任诞》。
[22] 见《世说新语·任诞》。
[23] 尼采著,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第一节。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页。
[24] 尼采著,孙周兴译:《悲剧的诞生》第一节。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页。
[25] 参见爱德华·布洛《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审美距离说”》,《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
[26] 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369页。
[27] 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760页。



(本文原载《中州学刊》2025年第一期)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