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
|
2010年2月18日 0:41:02
|
收藏本站 | 设为首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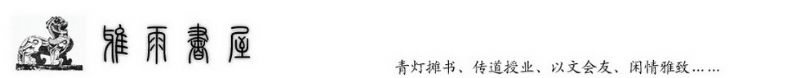
|
|

宁稼雨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
摘要:本文依据作者提出中国文化“三段说”学说,集中分析梳理作为中国士人文化时代重要时段魏晋文化的总体潮流精神。其中包括: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的规矩樊笼;以“道统”良知取代皇权势统控驭;以审美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人生态度。
关键词:魏晋文化 总体 潮流精神
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受到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质疑,但进化论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是难以彻底颠覆。受达尔文进化论和黑格尔历史哲学影响,西方学者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解析挖掘文学艺术产生动力和内在根源的视角,如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丹纳《艺术哲学》等对于文学艺术深层根源的挖掘,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文化潮流背景下的文学艺术产生发展动力与原因,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按照我本人关于中国文化划分为帝王文化(先秦两汉时期),士人文化(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市民文化(元明清时期)的“三段说”提法[1],魏晋文化是士人文化的起步阶段,因而在中国士人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演变历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魏晋士人文化取代帝王文化有其必然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先秦两汉时期曾经盛极一时的帝王文化,至汉末已呈颓势。连年不断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已经国家搞得千疮百孔,百姓民不聊生,朝不保夕,人心思变;在统治集团内部,由宦官外戚矛盾构成的深刻社会矛盾,更是引起局势动荡,群雄纷起。面对如此衰败局势,以往为帝王文化统治和管理的儒家大一统思想无力解释,客观上它促使国家思变。与此同时,在汉代社会矛盾和危机中乘势崛起的门阀世族却应运而生,成为新生社会主导力量。他们首先在经济上迅速膨胀壮大,并借此实力,在西晋国家危难之际,协助朝廷完成晋室南迁的壮举,并在江左协助司马氏建立东晋王朝,同时在政治上取得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地位,实现东晋门阀政治;与之相伴,代表体现士族阶层利益和观念的社会文化,也在玄学的引领下,逐渐形成魏晋士人文化的主旋律。魏晋士人文化的最大特色亮点,就是用个人色彩很强的全新士人价值观念和人生信条来取代此前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服务的帝王文化。其总体潮流精神理念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古老话题。从横向看,东西方在此问题上的认识各有所重,从纵向看,中国历史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和起伏。
西方人在此问题上似乎经历了一个“正反合”三段转折变化历程。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思想家一直非常强调精神对于物质的至高无上优越地位,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带来极大的物质生产飞跃进步和人们从中获得的极大物质享受,物质主义理论逐渐取代精神主义而占据上风。不过由于柏拉图的伟大深远影响,使得精神主义还难以完全退场。于是产生了将二者折中的二元论。这个过程反映出西方人在精神与物质问题上的思考和探索过程,但总体来说还是没有一边倒的绝对权威观点。
中国的情况与之有些不同。中国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精神物质二者关系的学说,但也不乏与之相关的理论学说建树。其中有两个方面与之关联比较密切,一是关于“义利”之争,二是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道器”之争。两个方面的共同点就是比较一边倒地向精神层面的“义”和“道”倾斜。先秦时期儒家十分强调“义”对于“利”的优越和主导地位,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3]等,并且明确提出“君子不器”的主张。道家则更是明确地主张把“道”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像老子提出著名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学说和庄子的“得意忘象”等等观点。都能明显看出先秦时期的重“道”轻“器”,重“义”轻“利”的观念为主流价值取向。
汉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注重物质的思想有所抬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事件,一是汉昭帝时霍光召集的盐铁会议,二是东汉时期王充提出的唯物思想。这两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物质观念做出相当力度的宣传和张扬,但在总体上还是没有能够达到将精神层面优势翻盘倒挂的程度。倒是曹操在长期掌管国家权力和军事征战过程中,迫切感到物质匮乏对于国家运转和军事作者的不利影响,因而大力推行屯田制度,强调发展经济和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社会价值暨社会地位。但这还只是社会实用的层面,从社会全局来看,“重义轻利”“道优于器”的观念仍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和颠覆。也正是因为这个大背景的缘故,才为承接而来的魏晋门阀士族以自身的发展历史来昭示精神大于物质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正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门阀名士,其主要关注点还是在社会政治方面。他们其中很多人在政治营垒上与曹魏政权有千丝万缕的瓜葛联系[4],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还对曹魏复辟抱有幻想[5]。这导致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司马氏政权的相处与对峙上,对发家致富一道物质追求似乎不大在意关注。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自我形象刻画中,已经透漏出其家境状况的清寒。阮籍所在的道南阮氏,更是如此:
阮仲容(咸)、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世说新语·任诞》)[6]
从这条故事中可以看出,其实重要的还不是道南诸阮如何清贫,而是他们对北阮富族的蔑视嘲讽姿态。这不仅是对传统“重义轻利”“道优于器”观念的继承,也是进入曹魏之后,门阀士族中在精神和物质观念上的一次公开分峙和对立。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竹林名士中虽然也有家财万贯者,但财富物质观念却不大像暴发户。像王戎虽然“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但同时却以吝啬闻名天下。更令人费解的还是他竟然对“钱”字讳莫如深: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世说新语·规箴》)[7]
从“洛下无比”的财产,到斤斤计较的吝啬鬼,再到闭口不谈“钱”字,这看上去反差极大的分极,其实也正是竹林名士在物质精神问题上的多方尝试。而这条故事中王戎是因为“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啄”才口不言“钱”字的。那么其以超然精神追求取代物质欲求的理念也是十分明确的。
到了元康时期,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高平陵事件曹党大批遭到镇压之后,司马氏已经彻底粉碎曹党复辟的希冀,将权力牢牢抓住手里。这使得社会上人们不再从这个角度关注社会政治;另一方面, 门阀士族在经济实力方面获得极大膨胀发展,享乐放纵成为相当流行的士族心态。正始名士的超然清寒生活态度被一扫而空,代之以骄奢淫逸的物质享乐生活态度。他们或者炫富斗富(王恺与石崇),或者为求美味以人乳喂猪(王济),或者以金沟划地为限(王济),或者以奢华厕所著称(石崇)[8]。这股以物质享乐为主题的风潮偏离了正始名士的超然精神追求方向,是门阀士族在精神与物质关系探索路径上的一段弯路。
东晋时期虽然偏安江左,但对于门阀士族来说却是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壮大机会,同时也使他们又重新回到重视超然精神追求的轨道上来。借助西晋南迁的机会,门阀士族不但辅佐司马氏皇权建立东晋王朝,而且自己也在此过程中获得巨大利好,在政治上获得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门阀政治局面。如此优越的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使得他们有机会,有条件来思考和实践更高层面——精神境界的问题。具体内容就是,他们意识到元康名士虽然为自己的物质享乐生活寻找到合理理由,但是却忽略了士族文人最根本最宝贵的东西——精神追求。为此他们一方面吸收元康名士享受物质生活的合理性部分,同时又提出更加重要的精神需求问题。与物质金钱享乐相比,超然的精神追求是士族文人的灵魂,更需要身体力行,奉为圭臬。
魏晋门阀士族文人对于精神物质关系的关注思考,经历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性思考,到为本社会阶层整体利益和权益去经营发展这一理念和实践的过程。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切身经历和体会中去思考和总结作为门阀士族阶层在精神与物质关系这个重要问题上应该给出的最终答案。这个答案的谜底就是:在经历清贫、富有两个物质极端方面之后,士族文人最终还是发现,只有超越物质层面的超然精神追求,才是自己这个阶层最本质的核心要素所在。
超然精神追求符合门阀士族文人阶层的社会属性和阶层利益。门阀士族不但是魏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主宰,而且也是魏晋社会文化的主流设计者与操盘手。从汉魏到两晋的社会发展历程看,门阀士族在完成经济实力的崛起和壮大,成为魏晋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之后,很快就凭借“九品中正制”成为社会上层[9],并最终发展成为门阀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政治主宰的局面[10]。凭借如此优越的社会政治地位,门阀士族很快把关注焦点从经济和政治转向社会文化方面。中国历社会社会史上很多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魏晋时期活得极大发展和突破,究其社会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门阀士族的社会需求和贡献所致。好
玄学不仅是中国思想文化在魏晋时期的重要发展阶段,更是代表门阀士族阶层根本社会属性和阶层利益的思想总结和精神诉求。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玄学不仅承续传统哲学思潮“重道轻器”的理念,尤其还能从老庄道家那里接过“大象无形”“得鱼忘筌”的理论认知,更加明确地提出“得意忘象”的哲学理念。无论是对于“言象”关系的探讨,还是对“象意”关的探讨,究其根本初衷,都是要强调“形而上”对于“形而下”的绝对优越地位。他们之所以如此看重“形而上”的价值地位,也正是他们从社会价值认知角度认为超然精神追求胜过物质欲求认识的哲学升华与表述。
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魏晋时期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繁荣,也正是玄学思潮统摄下注重精神层面追求社会思潮的代表和反映。从文学角度看,魏晋时期出现“文学自觉”,完成中国文学从与其他实用性文体中独立出来,树立起以纯文学形态出现,区别于其他文体形态的文学大旗。尤其具有说服力的是,“魏晋人向内发现了自己,向外发现了自然”,以抒发文人个人情怀,自我欣赏为主要特征的文人诗和用欣赏赞美自然美景的山水诗,成为这两个发现的重要成果结晶。
从艺术领域看,人物画不但取代山水画成为绘画艺术的主流,而且非常明确地提出“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的著名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视为玄学领域“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形而上胜于形而下一系列理论观点在绘画领域的贯彻和运用。而在书法领域,汉隶的工整和规矩被二王洒脱流畅的行书楷书所取代。都在从不同角度昭示出抽象对于具象,形而上对于形而下的优越态势和文化主潮。
作为这种文化潮流的外在表现和行为实践,魏晋士人的生活价值取向及其行为方式堪称鲜活的社会文化潮流标本。其内在表现就把玄学的“得意忘象”理论演绎成为注重精神层面追求,忽略物质层面占有享乐的社会思潮和行为方式。比如;: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箸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世说新语·雅量》)[11]
木屐与麈尾、宽衣大袖一起,构成魏晋名士风流外在服饰代表性标配样本,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生活价值取向的形象演示。这场钱财与木屐的较量中后者能够取胜,原因即在于此。
纵观魏晋士人生活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演变历史,可以清晰看出,物质与精神,金钱与情怀,一直是人们努力追求的两种人生目标和境界。但是历史最终给出的答案和结论是:笑到最后的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精神和情怀。
阮孚对于祖约的胜利,可以视为魏晋士人精神情怀与金钱物质两者对峙争雄的一个结果交代。与之相佐的事例还有: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世说新语·贤媛》)[12]
如果不了解那个时代背景,似乎很难在二者之中分出高下。但理解了当时文人价值观中形而上对于形而下的优势地位,就能清楚理解,王夫人对于顾家妇的胜利,也可以视为阮孚与祖约较量的另一版本演绎。可见魏晋名士在物质金钱和精神价值两者的占有和况味中有其发展变化走向趋向的话,那么非常清晰的走向就是自物质聚敛起步,而最终归宿于精神追求。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任何社会都难以平衡解决的难题,对于士人来说,这个问题又更加复杂和微妙。
按照社会学的一般理论,个体和社会这对矛盾双方各自有其存在和约束对方的理由和意义。从社会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统一的意志和规范,个性自由肆意泛滥,社会就难以维系和运行,所以必须主张社会统一意志;而从个人角度看,向往追求个性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而社会的规范又是扼杀个性自由的绳索,所以应该突破。正如社会学家的描述认定:
个人与社会共历巨变,使各自不同的诉求得以充分展现 —— 个人向往自由,社会需要秩序;个人要求权益自主,社会诉诸权力规范。如果说“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亚历山大),那么,在社会的秩序性面前,个人自由也难免不受质疑。个人和社会的各自诉求所表现出的一致与分歧、和谐与紧张、整合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性、风险性和危机性的根源,以至可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生活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13]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一个社会能否安定持久,这一对矛盾双方的拿捏和适应程度是决定要素。这个社会学发现的社会问题往往能够被社会文化的演进发展历史所证实。
我个人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体(个人)”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含义,其中物质是基础和条件,精神是升华和归宿。这里所谓“物质基础”,应该主要指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拥有程度(尤其是土地),而所谓“精神升华”则是指因拥有生产资料程度而产生的精神自由度。而“社会”则包括隐性和显性两方面含义,“显性”是指政府组织,“隐性”则是指大众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等。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对立关系,往往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关系的演变中去延续和变异。这样的思路线索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致能够得到验证。
自秦汉以来,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就一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但又相互抵牾状况。一方面,由于封建制和租调制等措施的推行,土地私有制得到巩固,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和崛起。受此背景影响,门阀世族的经济实力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一股重要的个体经济势力。这样的局面对于个性精神的滋长的确大有裨益。但是另一方面,以皇权为代表的国家社会方面也加强了社会对于个人的社会约束和精神统辖。如果说秦始皇的统一国土和度量衡是从物质层面表现出强烈的社会统一意志的话,那么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更是明确从精神领域提出社会意志的垄断意志。正是这个国家层面的决策,逐渐把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导向引入以儒家纲常伦理为基础的“以孝治天下”的社会潮流中。维护礼教成为皇权统治者理直气壮施行高压统治的依据和借口。从曹操杀孔融、祢衡,到司马昭杀嵇康,表面理由都是他们违背了礼教规矩,而真实理由却是他们的个性行为和思想触犯了自己的社会统治意志。这样,由社会经济发展促生的门阀世族势力崛起所导致激化的个性发展需求与皇权势力借国家道德伦理统一推行高压统治之间产生严重对峙和矛盾。但从社会时代潮流发展趋势来看,汉末以来社会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获得重要实力和发言权的门阀世族阶层,他们的个性意愿欲求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力还是远远超过皇权代表国家的社会约束力。所以,汉末至魏晋的社会文化主流,是代表门阀世族文人个人自由意愿突破代表国家和社会约束名教思想的崇尚自然精神。
能够体现和传达这种个性潮流取代社会潮流转变的社会现象突出表现在作为汉代统治根基的名教思想观念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个危机一方面表现在君权与君臣观念的淡漠,另一方面表现在家族伦理的危机[14]。东汉以后,随着门阀世族势力的扩张,以往知识分子直接的忠君观念逐渐被察举制及其“门生故吏”观念所取代。门阀大族成为未仕文人与帝王之间的屏风隔断,故而使未仕文人不但在出仕之前受到门阀故主的庇护和制约,即便出仕之后,也还要承担效忠故主的义务[15]。这就大大淡漠了文人与帝王之间的君臣义务观念,从而孳生出怀疑君权的行为理念:
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耶?”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后汉书·逸民传》)[16]
老者对于君王的鄙夷和揶揄,充分反映出当时君权观念淡漠的深刻影响,说明个人自由意识的觉醒和对社会意志的挣脱。怀疑君权思潮继续发展,也就自然生成无君论思想。鉴于天子们“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和“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的无道劣迹,阮籍公开提出“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无君论观点[17]。
与无君论相比,与社会普通人关联更大的是家族伦理危机。伦理本来是人类为维护正常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约定俗成的社会约定和行为规范,本身是人类脱离野蛮社会的进步表现。但到了东汉后期,儒家倡导的名教礼法已经被高度形式化的种种虚伪举动推向了反面。察举制度推动下的“累世同居”强化发展,把人们引导到为达到以“孝”名进身的目的,不惜弄虚作假。东汉赵宣以守丧墓道20年获得乡里重誉,却因同时在墓道生育5个子女被陈蕃处罚[18]。孔融任北海相时,将“哭泣墓侧,色无憔悴”的伪孝子处死[19]。这些状况引起重视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意识的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和激烈抗争。那个以四岁让梨著称的孔融竟然发出令人振聋发聩的呐喊:“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20]这些观念在社会上不断渗透延伸,以至导致魏晋时期士族文人强烈的个体突破社会群体,尤其是突破礼教束缚,寻求自然自由人生的文化潮流和人生境界。
首先是关于魏晋文人的自我意识。学界不乏关于中国文人缺乏独立人格和个性的说法[21]。对此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做具体梳理和分析。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个说法或许能够成立。但对此话题做具体分析时,就会发现反例情况。比如,纵观中国历代文人情态表现,还不能绝对说没有独立人格。从屈原,到陶渊明;从李白,到关汉卿。虽然可以对他们的独立自我意识打些折扣,但还是不能无视他们这种自我意识的存在。如果说这些人的自我意识只是个别人的个别表现,与所在时代的文人群体人格无关的话,那么即便就群体人格而言,也不能说是寸草不生。因为就文人群体人格而言,魏晋文人完全有资格被认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我意识。如果说他们与以往屈原、李白那些文人个性有什么区别的话,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对皇权和名教的态度。屈原、李白之流虽然以与皇权所代表的社会意志相龃龉,但他们与皇权的矛盾主要还是因为自己被人家遗弃之后的牢骚,骨子里还是儒家式的入世情怀。如同苏轼所言:“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而魏晋文人群体个性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是建立在与皇权所推行崇奉的统治个体自由的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名教”根本对立的态度之上。他们完全无视那个被儒家奉为至宝的“名教”,而只是迷恋那个最最宝贵的“自我”: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 [22]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世说新语·品藻》)[23]
用现在的话语表述,这些人大约都有些“自我膨胀”的意思。近年有学者注意到《世说新语》这部“名士教科书”中广泛使用了具有多种内涵的“我”字[24],应该也完全可以从自我意识觉醒的角度来理解。正是因为“我”字当先,才使得他们无处不在强化突出自我,表现自我: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处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25]
无论是“翳然林水”,还是“鸟兽禽鱼”,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只能在于其是否能够被人的“会心处”所感应,都只能依据是否能够“自来亲人”来判断。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到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在这个微小故事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当然,自我意识的最高表现不是会心自然山水,而且人自己的生命。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王濛临终前“如此人,曾不得四十”的哀叹,都是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表现。更有甚者,则是将自己的生命价值形象物化: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世说新语·雅量》)[26]
嵇康生命结束之际,就是《广陵散》绝迹之时。一曲音乐成了一个人格的生命化身。魏晋文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堪称登峰造极,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名教危机下的魏晋士风是最近于个人主义的一种类型,这在中国中国社会史上是仅见的例外,其中所表现的‘称情直往’,以亲密来突破传统伦理形式的精神,自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即士的个体自觉。”[27]
伴随自我意识就是频繁而充分的个性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狂放举止。西周时期随着礼制的完善,人们的各种行为方式都有了规范标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社会约束是人类告别动物,走向文明的社会进步。按照这样的社会约束,狂放举止显然在受到约束之列。但自秦汉中国进入大一统格局后,这些代表文明进步的礼制礼仪逐渐被其掌管者操控,使之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尤为突出明显的就是汉代以来将以伦理为中心的礼教名教高度政治化,用符合礼教精神的伦理标准作为人才选拔,社会舆论,价值观念的首要衡量准绳。这种假公济私的虚假“社会意志”必然遭到其管束对象的激烈反响和对抗。而反响对抗的外在表现便是用狂放举止去冒犯他们所推重的名教和礼教。这一点在竹林名士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刘伶狂饮,以至亵渎神灵,裸体现形,意在抨击礼教代言人“缙绅处士”;阮籍母丧饮酒,近嫂攀谈,明示:“礼教岂为我辈设也!”故而最终嵇康喊出他们的共同心声——“越名教而任自然”!相比之下,嗣后元康名士虽然其狂放行为比竹林名士更为夸张,但是其狂放行为反礼教的态度却大大减弱。不过尽管如此,他们的狂放行为却足以颠覆名教笼罩下的社会风气: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刘注引王隐《晋书》: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坦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世说新语·德行》)[28]
与之相类,“八达”裸体与猪同饮[29],周顗当众欲通纪瞻爱妾[30],均可见狂放何等之极。
其次是奇异怪癖行为。此举虽然力度不及狂放夸张变态,但也足以颠覆挣脱名教社会束缚之牢笼。汉代以礼教伦理为核心的社会共性约束,逐渐引起人们逆反心理,希望挣脱其绳索控驭。于是,从东汉开始,求新求异成为社会潮流。为了求新求异,有时甚至不断在正反两极中跳动游移。汉末樊英努力按传统社会形象标准打造自己,言行谨饬,但最终因为“无奇谟深策”之异,竟然遭到僚毁谤布流[31]。此乃由“同”至“异”之路。可一旦求新求异演为社会大潮,又会有人由反回正,由“异”回“同”。据《后汉书·袁阆传》,袁阆致名当世,并非因为追异猎奇,相反倒是因为能在众修异行者中卓然相反,以不修异操致新颖行为而名闻天下。这样的反复跳跃的求新求异风气无疑催生了众多奇异怪癖行为,彰显出纷纷总总的特立独行个性怪癖行为。姑举几例,以窥全豹。
一为以口技形式学驴叫。这个有伤大雅的怪癖行动居然频繁发生在汉末以来的上流社会中。据载东汉大名士戴良的母亲喜听驴叫,戴良为表孝心,竟然经常为母亲学驴叫以取悦其心[32]。不过最常见的学驴叫行为还是经常发生在送葬活动上,比如王济生前一直很喜欢听孙楚学驴叫的表演,王济去世后,诸位大名士均来吊唁送葬。可孙楚却选择了一种最为特殊,但却是王济本人最喜欢的方式——用驴叫给王济送行。用驴叫为逝者送行在那时好像也并非空谷足音: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世说新语·伤逝》)[33]
堂堂魏文大帝,竟然带着满朝文武,齐声学起驴叫,以寄托对王粲的哀思。毫无疑问,可以想见这奇葩的举动在朝野能够引起的轰动效应是何等炸裂。
二为类似今天打口哨的长啸。说到打口哨,今天人们一般会联想到那些街头混混或嬉皮士之流。大概谁也不会想到,那时曾经风行一时口哨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阮籍: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生僻字(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世说新语·栖逸》)[34]
看过并理解了这个故事,便会顿时明白,阮籍的口哨与那些街头混混和嬉皮士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本条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和《竹林七贤论》,阮籍从这位真人的啸声中悟出人生自由的真谛,挥笔写出《大人先生传》来展示其思想的飞跃。这个思想到行为的示范效应果然奏效。从阮籍开始,“啸”这种口哨闲散形式竟然成为士人抒发自由性情的媒介形式,因而格外热衷。谢鲲因挑逗邻家女子,被人打掉两颗门牙,还遭到人们编出歌谣取笑:“任达不已,幼輿折齿。”可谢鲲关心的却是折齿后还能否长啸:“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35]原因即在于歌啸能够宣泄情感,抒发个性自由。谢安面对惊涛骇浪,“神情方王,吟啸不言”[36];王徽之见到喜爱竹园,则要“讽啸良久”[37]。如此风气竟然把歌啸之美弄到令人痴迷的程度。一位老妪因为痴迷刘宝歌啸,竟然把他请到家里,杀了一头猪来招待刘。但刘宝吃了一头猪,还是没反应。老妪只好再上一头。第二头猪刘宝实在吃不完,吃了一半,终于开始用歌啸答谢[38]。
三是以率真举动展示个性。率真行为成为潮流新宠,是为了对抗礼教束缚下的虚假面孔。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集中阐明自己之所以不肯入朝为官,就是无法忍受官场那一套虚假繁文缛节和模板面具淹没自己个性习惯的悲剧。阮籍在《大人先生传》里也对“唯法是修,唯礼是克”的套中人予以无情嘲讽和鞭笞。他们二人如此态度不仅表现在文章中,更是表现的许许多多率真的行动上。嵇康因冷落钟会而得罪小人,终于丢掉脑袋;阮籍主动求官步兵校尉,竟然为了橱中美酒。一时间,丢掉面具枷锁,坦露真实个性成为很多人的行为方式选择。荀粲直言“妇人当以色为主”,自己冻冷身体为发烧妻子降温[39];王悦与父亲下棋,竟然按住父亲举棋之手[40]。这方面比较突出有两位,一个是王戎。他不但挖去自家好李的种核出售,而且还在小资小钱方面与晚辈斤斤计较。可一旦中年丧子,则悲痛欲绝,自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41]
另一个是王述。他的率真个性堪称绝佳。当王导手下一群人对其大唱颂歌时,唯独王述站出来大唱反调:“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42]当他自己受命尚书令一职任命,马上就接拜。儿子在一旁劝他:按惯例应该客气谦让一下。他便振振有词地反问,为啥要谦让?你决定我能否胜任?能胜任为啥还要谦让?一副纯真见底的书生相[43]。但最能反映王述率真性格的还是他那个著名的吃鸡蛋故事: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世说新语·忿狷》)[44]
这位怒得可笑,而又十分可爱的蓝田大哥,会让每个读者都会燃起跟他交朋友的欲望。
与个性活动相关,还有文人交往中的个性表现。个性的展示往往需要在对比和映衬中去实现,所以交往是文人个性实现的重要渠道。只是这样的交往一般要通过两个渠道,即和谐和冲突两种外在形式去展现。
促成魏晋文人和谐交往中展示个性的机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人雅集。很多文人集会活动是他们展示个性的极好机会。建安七子和曹氏兄弟的西园之会,西晋时期石崇邀集的“金谷之会”,东晋时期王羲之与谢安等人发起的“兰亭之会”,文人们在交流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各自的个性和才华;二是人物品藻活动。汉代以来人物品藻活动随着评价标准的游移变化,其对于文人个性的导向和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汉代在儒家思想统摄下,人物品藻评价标准以品德(尤其是“孝”)为核心。从这个角度看,此时人物品藻活动对个性抒发实际上是违和甚至戕害的作用;但从曹魏开始,“唯才是举”打破并改变了人物品藻活动的评价标准。对人物才能的关注和重视显然有利于对于文人个性的开发和推动。嗣后,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人才选拔已经失去对人物品藻评价结果的依赖。于是,人物品藻的标准又从注重才能转向注重审美。而人物审美评价又更加刺激了文人个性的展示和爆棚:
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双眸闪闪如岩下电。
濯濯如春月柳,谡谡如劲松下风,朗朗如日月之入怀。[45]
这些美好的形容词句,把不同人物的美好个性神态,淋漓尽致地描绘勾勒出来。如果说这种评价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发现并展示别人的个性的话,那么还有许多人在评价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带入其中: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世说新语·品藻》)[46]
评价别人其实只是自己个性展示的一个平台。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建立在相互了解至深的基础之上。王濛和刘惔这一对清谈大师就是如此。王濛曾深深感慨道:“刘尹知我,胜我自知。”[47]评价别人和自我评价的相互换位,能够在映衬对比中把各自个性特征表现得更加充分和彻底:
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頠、乐广友善,遣见之。頠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 (《世说新语·品藻》)[48]
两位品藻者不仅评出了被评者的个性特征,而且还融入了自己本人的主观个性色彩。堪称精彩的个性对决比拼展示。
门阀士族经济崛起和政治膨胀,导致很多士族文人自信心爆满,个性膨胀,从而也助长了他们性格中的排他性。而同样的人相互接触,也就容易引发与他人交往中的龃龉现象。如阮籍擅以青白眼面对好恶不同之人[49],谢奕因小事遭王述冒犯,竟然“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50],桓温与袁耽樗蒲赌博,“袁彦道齿不合,遂厉色掷去五木”。更有甚者,有时有人脾气暴躁,还能发生肢体碰撞:
王司州尝乘雪往王螭许。司州言气少有牾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觉恶,便舆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讵复足与老兄计?”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 (《世说新语·忿狷》)[51]
一场好好的朋友聚会,竟然因为一言不合,便反目翻脸,动起手来。与下面的故事比,这个还只能算是小巫:
王大、王恭尝俱在何仆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大逼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世说新语·忿狷》)[52]
朋友之间竟然因劝酒而险些酿成千人群殴事件,足见各自个性之强盛。
魏晋时期文人个性的群体涌动是中国文化史和文人心态史的重要现象。对于反思中国士人历史,对照现状情况,均大有裨益。
(未完待续)
[1] 参见宁稼雨《中国传统文化“三段说”刍论》,《求索》 2017年第三期特稿。
[2] 《论语·里仁下》,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267页。
[3] 《论语·卫灵公下》,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9页。
[4] 阮籍的父亲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曹操集团的重要谋士。嵇康的妻子又是曹操曾孙女长乐公主。
[5] 参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6] 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732-733页。
[7] 刘义庆《世说新语·规箴》,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557-558页。
[8] 均见《世说新语·汰侈》。
[9] 参见唐长孺《士族的生成和升降》,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 参见田馀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飞出版社1989年版。
[11] 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356-357页。
[12] 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699页。
[13] 郑杭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江苏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1 期。
[14] 说详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 参见杜佑《通典》卷六十八、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88年排印本。
[16] 范晔《后汉书·逸民传·汉阴老父》,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排印本,第2775页。
[17] 参见阮籍《大人先生传》,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
[18] 参见《后汉书··陈王列传》,中华书局1977年排印本。
[19] 见《太平御览》二百六十二引《秦子》,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20] 范晔《后汉书·孔融传》,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排印本,第2772页。
[21] 参见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载《新华文摘》1987年第二期。
[22] 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521页。
[23] 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522页。
[24] 袁济喜《<世说新语>之“我”与魏晋社会风景》,《学术界》2023年第九期。
[25] 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120-121页。
[26] 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344页。
[27]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8页。
[28] 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24页。
[29] 见《晋书·光逸传》。
[30] 见《世说新语·任诞》。
[31] 见《后汉书·樊英传》。
[32] 见《世说新语·伤逝》刘孝标注。
[33] 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636页。
[34] 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648页。
[35] 见《晋书·谢鲲传》。
[36] 见《世说新语·雅量》。
[37] 见《世说新语·简傲》。
[38] 见《世说新语·任诞》。
[39] 见《世说新语·惑溺》。
[40] 见《世说新语·排调》。
[41] 见《世说新语·伤逝》。
[42] 见《世说新语·赏誉》。
[43] 见《世说新语·方正》。
[44] 刘义庆《世说新语·忿狷》,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886页。
[45] 均见《世说新语·品藻》。
[46] 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522页。
[47] 见《世说新语·赏誉》。
[48] 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507页。
[49] 《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晋百官名》。
[50] 见《世说新语·忿狷》。
[51] 刘义庆《世说新语·忿狷》,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887页。
[52] 刘义庆《世说新语·忿狷》,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888-8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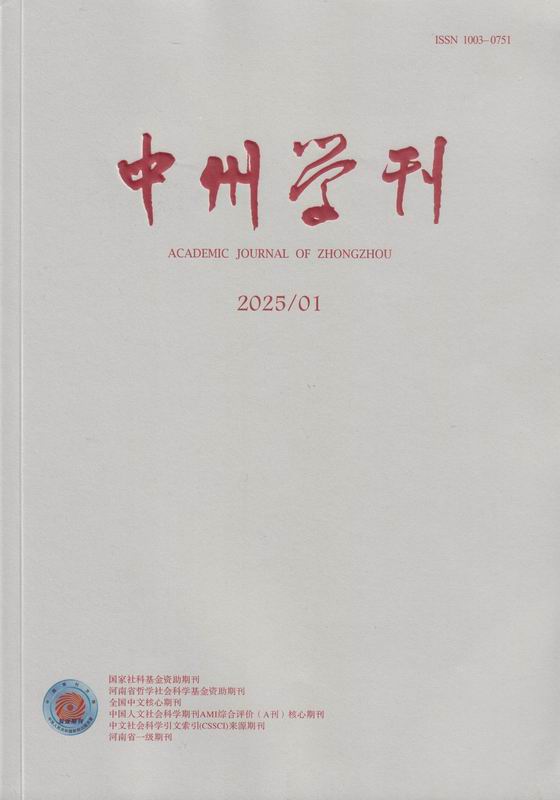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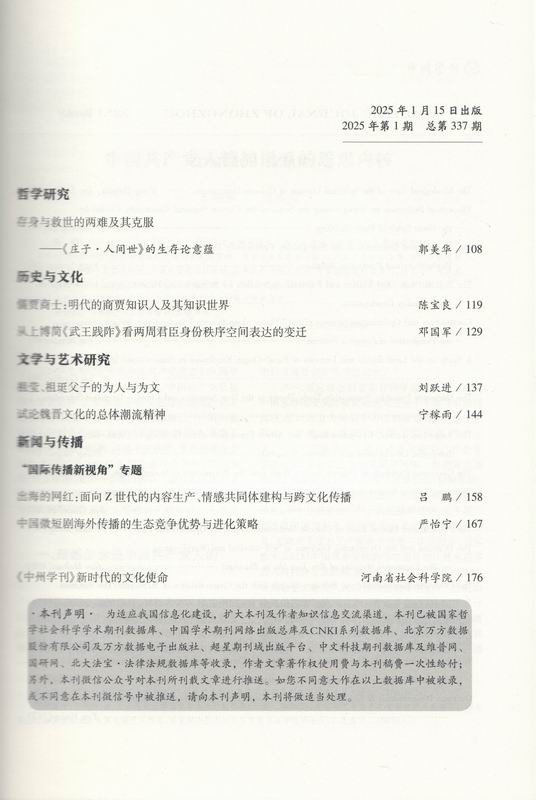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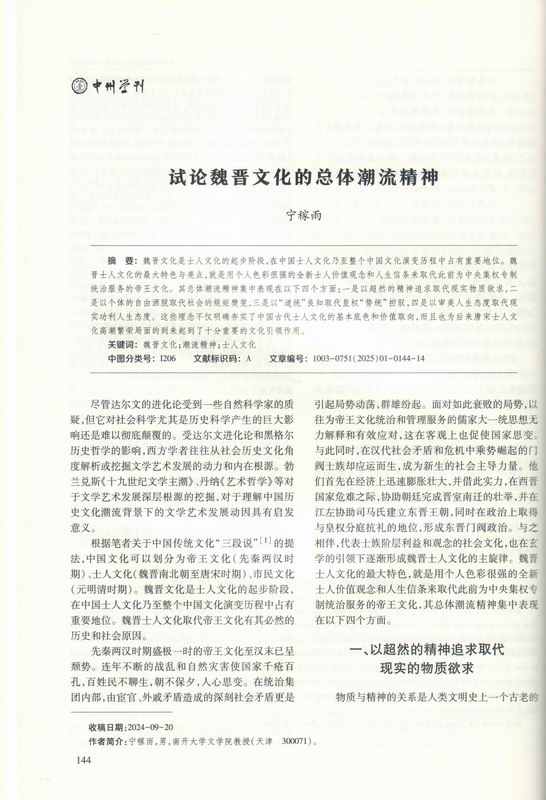
(本文原载《中州学刊》2025年第一期)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
宁稼雨的雅雨书屋 网址:http://www.yayusw.com/ 备案序号:津ICP备10001115号 本站由中网提供网站空间与技术支持,马上申请与我一样的网站 站主其他网络园地:雅雨博客|爱思想网个人专栏| 中国学术论坛宁稼雨主页|南开文学院个人主页|中国古代小说网个人专栏|明清小说研究宁稼雨专栏|三国演义网站宁稼雨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