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风度的蕴含与价值
宁稼雨
明末著名小品文作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这话即便在今天也足可引起很多人的认同乃至共鸣,原因就在于“深情”和“真气”乃是人间珍奇之物。能将此二者纳入其中,任意挥洒,成为癖好,乃是人间上等好事。
历史上以时代而论,癖好多得难以计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则非魏晋莫属。像饮酒、服药这些稍微大众一点的癖好自不必说,有些癖好简直让今人情何以堪:养马癖、养鹤癖、喜竹癖、宽衣大袖癖、木屐癖这些也还算雅致;可像豪华厕所癖、与猪共饮癖、当众露阳癖这些可就有点令人咋舌了;更有甚者,还有些人要么深深恋上了驴叫,要么干脆以裸体为常……
如果从张岱的视角逻辑来看,这些癖好当中理应蕴含着深情和真气——果真如此吗?
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决定性的重要原因就是:包括以上所有这些癖好在内的魏晋风度整体,那些由众多名士各种生活行为组合而成的被称为“魏晋风度”的东西,本身也已经成为后代许许多多文人雅士十分钟爱和向往的一种癖好:或者叫做“《世说》癖”(一部囊括魏晋风度的“名士教科书”),或者叫做“魏晋风流癖”。
那么,“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它的深层蕴含了哪些奥秘?它何以能够在历代文人心里占有如此沉重的份量?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又具有何等价值,占有何等地位呢?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五彩缤纷的多种颜色和风格。魏晋风度是其中风格独特的精彩亮点。它不仅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独领风骚,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现实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魏晋风度”概观
魏晋风度,又称“魏晋名士风度”,指魏晋时期以门阀士族文人为主体的知识阶层在玄学思潮引领下,以生活言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具有深刻文化蕴含和独特别致趣味的气质风采。它的核心理念是“道优于器”(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它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化史的走向,还是对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念构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从古到今,人们之所以对魏晋风度钟爱有加,有它内在的、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各个时期人们不同处境对魏晋风度某些方面的向往之处。
中国古代的主流人格理想模式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可以说是儒家式理想的人生模式。达也好,穷也好,实际上说的是两种状态。但是作为儒家人格理想来说,主流方面还是强调要为社会服务,要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理想。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绝大多数的古代士人们所持有的一个共同的主流理想。但是,为什么还提到了一个“穷”?从思想的角度来说,除了儒家的主流思想之外,我们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等等其他思想?我想主要是因为儒家这条路是古代人们设计的最理想的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利地在这条路上走得通、走到底的。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要从社会考察,或者科举考试一步一步地爬到人生顶端,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所以在不能人人实现终极人生理想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其他思想来进行调节、平衡。而道家思想、道教思想,包括佛教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种平衡的作用。
李泽厚先生把我们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总结成两个方面,他说叫儒道互补,其实是儒释道互补的,这三者互补的。怎么样的互补?就是儒家强调入世精神,我们要为社会去服务、贡献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在某种情况下,不适意、不得志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种来调节自己心态的方式,或者说一种人格模式,这就是道家思想或者佛教思想。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魏晋风度为代表的人生的另外一种模式——自己安顿自己的模式,产生了。它既不完全为儒家的理想走到底,也不按照道家佛教的思想走到底。魏晋风度要把它们都融合起来,让各种思想最大效能地为我们的社会,也包括为我们每一个个人去打造、去营建、去形成一种我们面对社会时正确的心态和观念。
二、“魏晋风度”的内涵与表现
魏晋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后面我还要专门说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魏晋文化,它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魏晋风度的文化涵盖面非常广泛:政治、经济、文学、宗教、语言、社会、风俗等等。有意思的是,在《世说新语》这本被鲁迅称为“名士教科书”的书里,几乎可以了解到所有关于魏晋时期各个方面的文化背景故事,具体感受到魏晋风度的形象写照。
在多年教学和科研经历的基础上,我把对于魏晋风度为代表的魏晋文化做了一个综合的归纳和总结,把魏晋文化的总体精神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
第二,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和樊笼。个人和社会,是个人服从社会呢?还是社会任凭个人自由的驰骋?
第三,是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世统控驭。知识分子,他始终和政权有这种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很早就解决了,教会是政教合一的。中国等于政府和士人分别承担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政权,一个是真理。在西方好像教会是把这两个东西整合在一起了,那中国这两个东西是分离的,所以就出现了士人的道统良知怎么去取代皇权的世统控驭。这个问题,在魏晋时期有它特殊的解决方式。
第四,可以说是前三点的一个整合和归纳,是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
魏晋风度大致分为三个层面:即社会层面、行为层面、精神层面。
社会层面
社会层面是指从社会风气和社会氛围中体现折射出的魏晋名士风采。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魏晋门阀士族阶层的崛起及其相关的门阀观念在名士群体生活中的表现;二是名士在人物品藻风气所展示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有两件令人瞩目的大事,一是所谓“盛唐之音”,二是所谓“文学的自觉”。一般来说,人们是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说,分开来看的。但如果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轨迹上看,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个因果关系。换言之,如果没有魏晋时期以世族文人的社会地位独立为基础的文学自觉,盛唐时期以文人为核心的文化繁荣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文学自觉的前提是文人的人格独立,其主要内涵就是魏晋时期门阀世族在经济政治力量发达基础上文人的人格地位的充分提高。世族文人经济实力的膨胀,导致了以所谓“门阀政治”为特征的政治地位的确立。正是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的实力强大,才造成了魏晋时期世族文人的群体人格的独立;正是这种人格的独立意识,才是文学走向独立的基础和前提;正是文人的人格独立和文学自身的独立,才是“盛唐之音”的源头之水。
关于门阀士族,历史上有过不同的评价和定位,主流声音是批评和否定,理由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社会方面来说,门阀士族操纵了社会人才选拔的渠道,形成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人才发展独霸现象;从个体角度来看,处于上升时期某些门阀贵族的奢侈堕落生活方式给人们留下非常不好的负面印象。但从历史的情况看,门阀士族在其历史发展中还是有过很多重要的历史文化贡献。西晋灭亡之后,皇权已经奄奄一息,东晋王朝完全在以王导为代表的门阀士族阶层支持下,才建立和巩固了东晋王朝。另外,正是门阀士族的努力,中国历史上人们的关注焦点才第一次从社会和国家,进入到关注和肯定个人价值和意趣的层面。
人物品藻,就是对人物的德行、才能、风采等诸方面的评价和议论。它是汉魏六朝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如同战国时期诸侯养士引起游说之风,明清科举制度引起八股之热,统治者的选举与用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引导了广大士人的行为选择。汉魏六朝时期的荐举入仕的方式是当时人物品藻风气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又形成了相同或相似的用人方式下不同的人才价值标准;不同的价值标准,又对希望入选或希冀名声的士人言行,产生不同的刺激作用。反过来说,通过士人的言行,来考察当时的人物品藻风气,会得到更为真切而生动的感受,观察到一幅活龙活现的历史画卷。人物品藻活动的重要历史价值在于,它由最初社会人才选拔的途径,逐渐转变为对于人物、自然、山水,艺术进行审美评价鉴赏的整体观照,对中国文学艺术评价和鉴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宗白华先生所讲:“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由人格美的评赏。”
行为层面
行为层面是指具体到名士个人的种种生活和行为方式,如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活动等。其中最能体现出魏晋风度特征的几个方面分别是:饮酒活动、服药活动,服饰行为,休闲娱乐活动等。
饮酒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有关魏晋名士饮酒的评价和看法却往往截然相反。道学家认为魏晋名士饮酒不仅耽误了国家大事,而且那种酒气熏天的样子也实在不成体统。鲁迅和王瑶先生却对魏晋名士的饮酒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见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导致对同一问题的相反看法。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对于魏晋名士饮酒行为的认识,也许不必在是非问题上强分轩轾,而是从认识的方面了解其形态面貌,尤其是其饮酒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演变轨迹。
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饮酒活动的基本走向是社会和群体意志的色彩逐渐淡化,而个人和个体意愿的色彩却不断强化。具体来说,魏晋时期文人饮酒的变化轨迹是,其一,饮酒从祭祀天神宗教性目的,变而为文人进入自己理想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导引性媒体;其二,饮酒从周代礼制统治强调社会的尊卑秩序和伦理精神,变而为部分文人宣扬反礼教思想的重要行动;其三,饮酒从养生(包括养老和养病)的初衷,变而为文人及时行乐的手段和内容;其四,饮酒从西周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对其社会政治作用的担忧,变而为名士回避政治的有效借口。这不仅使魏晋文人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极大的个体色彩和人文精神,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饮酒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大约从汉代开始,中国士人阶层风靡一种叫做五石散(又称寒食散)的药物,可是说来奇怪,这种药物很难说它对某种病有什么特殊疗效。可是大家却趋之若骛,争先恐后地来效法和实践。到了魏晋时期,这股风潮更是达到了顶点。一时间,人们把服药看成是门阀世族的时髦外在特征。不服药,好像就今天的人们不会用手机,不会上网一样土里土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药,人们为什么对它如此情有独钟呢?
作为士族神仙道教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士族文人服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逍遥和肉体上享乐的需要。《世说新语》中士族服药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它与帝王服用丹药和民众服符的不同,而且还集中体现了士族神仙道教中的“地仙”思想。
魏晋时期神仙观念较之前代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们把求仙和成仙的着眼点,从遥远和飘渺的上天和海外神山,转入到自己生存的环境周围,转入到自己个体的精神和肉体建设上来。当时士族阶层所普遍热衷的“地仙”说,就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这样的观念转变。所谓“地仙”说的核心,就是想方设法以求长生,以迎合门阀士族享尽现时荣华富贵的需要。尽管先秦以来各种求仙之法层出不穷,花样翻新,但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成仙法术的内容和需求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寄托。就服药一项而言,秦汉时期一些帝王服用的主要是丹药,其目的是为了在自己身体的不死上面寄托长久统治的希望;汉末以来下层民众中主要盛行的是服符和乞灵巫祝之道,而且这些东西往往被用来作为组织串联并聚众起事的工具;而魏晋时期士族文人中主要服用的是石药,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逍遥和肉体上享乐的需要。《世说新语》中士族服药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它与帝王服用丹药和民众服符的不同,而且还集中体现了士族神仙道教中的“地仙”思想。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部分,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但衣食住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它的变化,不仅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也是他们精神追求的物化表现。所以,通过衣食住行,我们往往可以清晰地把握一个时代的潮流走向和精神脉搏。
士族文人是魏晋六朝这一时代舞台的主角。士族文人的衣食住行,便是魏晋时代潮流和精神脉搏的折射镜。作为士族名士的教科书,《世说新语》广泛反映了士族文人的各个生活侧面。其中包括他们不可须臾离开的衣食住行。其中主要包括能够集中体现士族文人精神变迁的服饰、饮酒和娱乐活动三个方面。
服饰的风俗在魏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显著特征是: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尊崇礼制的色彩不断淡化,而反礼教的叛逆色彩不断增强,此其一;其二,人们在穿着服饰方面的物质层面的需求不断淡化,而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最能体现这些潮流变化的是服饰方面的“服妖”行为、宽衣大袖、木屐、裸坦行为,以及麈尾和如意等饰物。
一群衣食无忧的贵族,一群精神追求胜过一切的文化人,所能激发的多半是艺术的热情,所能创造的,也多半是灿烂的文化业绩。在文人的群体独立完成以后,他们便醉心徜徉于形而上的世界中,以其神超形越的智慧,于阿堵种种中得传神之笔,绘出一幅幅洛神之图,写出一篇篇兰亭之序。中国文化因此而灿烂,中国艺术因此而骄傲。
魏晋文学艺术极富特色。它不仅是对先秦两汉文学艺术的继承和总结,其由“人的自觉”带来的“文的自觉”,更是为这个时期的文艺从题材内容到表观形式都开辟了极为广阔的领域,从而孕育了盛唐的文学艺术高潮。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可能详尽而充分地了解魏晋文人生活行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但通过现存的部分材料,仍可以在部分文人的生活行为中,窥见这个时代文学艺术转换的契机和状态,以具象的内容,去感受和把握宏阔的历史文化氛围。其中比较重要的文人聚会活动有:建安文人邺宫西园之会,西晋名士金谷之会,东晋名士兰亭之会等名士雅集活动,通过这些集会活动,魏晋文人的两种审美意识,以及他们在诗歌、散文、绘画、书法、音乐等诸多文学艺术领域的具体活动形态得到深入表现和传达,从中能够窥视魏晋名士文学艺术活动所展示的魏晋审美意识和文化蕴含。
此外,最能体现魏晋风度行为层面的表现还有魏晋名士的隐逸行为。隐士的政治生活,突出表现在他们与皇权的关系上,隐士形成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士人的独立意识,即“道”优于“势”的信念;二是皇权所希望的隐士的社会使命,即在皇权与社会的矛盾中起到协调作用。这就决定了隐士与皇权间无所不在的紧密关系:皇权一方既要用隐士来装潢门面,又要避免隐逸之风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隐士一方又要追求独立意识,又不得不承认为人君之臣民的现实,即尽管“道”优于“势”,可又不得不服从“势”的绝对统治。于是,双方如同一对命里注定的冤家,互相排斥,而又互相吸引。
经过前代的教训,魏晋时期的皇权与士人都开展了对双方关系相处方式的思考与研究。其活的标本,便是“竹林七贤”。
精神层面(玄学“言意之辨”与魏晋名士“得意忘象”人生态度)
从精神层面来看,当时思想领域主流的东西就是玄学思想,玄学思想有很多的大家讨论研究的命题,比如说“有”和“无”,“言”和“意”的关系等等。这里主要说说玄学的“言意之辨”在魏晋风度中的具体表现。
所谓“言”和“意”关系的讨论,其实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主要讨论的话题就是语言能不能够把我们要传达的事物的内在内容或者思想准确、周延、充分地表达清楚。一种人认为不可能,所以这种人的观点叫做“言不尽意”;另外一种人认为“言可以尽意”;第三种人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是“得意忘言”。
之所以要探讨这个问题,和当时玄学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有关系。当时玄学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周易》的每一种卦象所代表的意义内涵。如何用语言把卦象说清楚,而卦象又有什么样的内在意义,是出于这么一种需要,来重新探讨言和意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发展过程当中,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我们前面了解到的很多故事到最后都归结到哲学的层面了。大家更加认可的言意关系的解释叫做“得意忘言”。我们在了解一个事物的时候不能没有语言。第一,我们了解事物需要语言来表述它。第二,语言不是我们了解事情的目的,语言是一个工具,工具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内在思想和意蕴,一旦我们对内在意蕴了解清楚之后,语言就成了多余的东西,这就叫“得意忘言”。虽然这说的是哲理问题,但是我们从魏晋名士的生活当中可以看到,实际他们对言意关系的把握已经完全渗透到人生的每一个角落中,他们把人生的每一个方面都从言和意的关系上去理解。我们人生终极的最有意义的目的就是言意之辨当中的“意”。那什么是“言”?就是外在的、表面的形式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要上学,要拿学位、要工作、要交朋友等,所有这一切在魏晋名士看来,都是形式的东西,人生最重要的内容是我们看不见的内在意蕴。
社会层面的“得意忘象”人生态度
下面这个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得意忘象”的人生态度: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
张季鹰(张翰)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当时人们用“得意忘象”的思想来指导人生的行为。对于张季鹰(张翰)来说,什么是“象”?显然“名”是象,是表象的东西,是外在的东西,不是人生终极的目的,而对他来说人生终极的目的就是眼前的快乐。这是从表层的社会层面来理解什么叫做“得意忘象”。包括下面,张季鹰回老家吃鲈鱼脍、莼菜羹。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世说新语·任诞》)
哲理层面的“得意忘象”人生态度
哲理层面的“得意忘象”,就是从哲理的角度出发,在纷纭复杂的人生当中,发现一些内在的意蕴、道理、趣味,来体现一种“得意忘象”的态度。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世说新语·言语》)
刘尹与桓宣武一起听讲《礼记》,桓温说他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最有意蕴的东西,他已经感悟到了。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见《世说新语·言语》)
支道林喜好养马。有人说,你作为一个僧人养马,这好像不大合规矩。支遁说我是“重其神骏”。也就是说对他来说,养马韵和不韵,合不合乎世俗看法不重要,因为支道林在养马的时候,他所关注的是骏马驰骋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恰是他思想上所要去追求所要去追寻的境界。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见《世说新语·言语》)
支遁不但喜欢养马,还喜欢养鹤。有人送了他一对鹤,过一段时间鹤翅膀长长了,想飞。支遁说你别飞,你飞了,我鹤就没有了。支遁就用剪刀把鹤的翅膀给剪掉了,鹤飞不动了。“轩翥”是扑腾翅膀飞不起来了,同时它回过头来看着自己的翅膀低下头来,“视之,如有懊丧意”,它看着自己翅膀飞不起来了,很伤心。这个时候支遁说,“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它有凌空万里、飞向九霄云外的这种能量,它怎么能够甘心给别人做耳目近玩,做一个宠物,养在家里。于是之盾把鹤的翅膀又养好了之后,让鹤飞回了蓝天当中。
这个事件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就是在简单的生活行为当中,生活细节在他们这里都有哲理的追求,他们都有哲理来指导人生。
审美层面的“得意忘象”人生态度
第三个层面是审美层面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得意忘象”的人生态度这个事最高的一个境界。
将摆脱社会名教束缚的人生快意说与“得意忘象”的人生哲理说的结合,就自然形成了魏晋士族文人的审美人生观。审美人生的最大障碍是人对于人生过程功利和实用的取向。关于这一点,《庄子》里面有个故事: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
庄子发现有个大树根。通常看一个木头有没有用,要看它能不能做成房梁,破成木板。但是庄子说,他在深山里面看到有一种东西,大树根乱七八糟的,什么也做不了,做不了门窗也做不了房梁,没有实际用处,但是它有重要作用——审美的作用。今天有很多艺术家,特别是根雕艺术家,拿大树根来做根雕。对于有用和没用的评价,到底是什么?从实用的角度来说,直直溜溜的成材的有用,但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树根有用。和刚才庄子所讲的意思是一样的,有用的东西很难实现审美,而审美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排除实用性的功利性的目的。
孙绰赋《遂初》,筑室畎川,自言见止足之分。斋前种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远时亦邻居,语孙曰:“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孙曰:“枫柳虽合抱,亦何所施?”(《世说新语·言语》)
文中两个人不同在哪里?一个是从实用的角度,高世远的衡量标准是能不能做门窗、房梁,而孙绰说他对这些实用的东西并不关心,他的标准是美不美。
整个《世说新语》,整个魏晋风度,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篇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王子猷(王徽之)居山阴(绍兴),晚上下大雪了,他醒了,把窗户打开,吩咐下面的人说,上酒。他打开窗户,四面一望,四望皎然,漫天洁白大雪,多么富有诗意的一个场景。看到这四周白茫茫的雪景,王徽之“因起仿偟”,于是他又在吟咏左思的一首很有名的诗叫《招隐诗》。吟咏着左思的《招隐诗》,他突然想起他的好朋友,叫戴安道(戴逵),可是当时戴逵并不在山阴,他在山西。他说我要马上见到我的好朋友戴逵,马上就要准备船,“夜乘小船就之”,马上连夜开着小船就去找他的远在山西的朋友戴逵那去了。“经宿方至”,小船跑了一个晚上,“造门不前而返”。到了戴逵家门口,没进门,王徽之打道回府,不进去了,别人就傻了。我们来看他的解释,就是典型的能够传达代表魏晋名士“得意忘象”人生态度的最经典的一个解读。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晚上所有的行为都是在干嘛的?“兴致所至”,全靠兴奋点来驱使,想赏雪了就赏雪,想喝酒了就喝酒,想去看朋友了就坐上小船就去看朋友,可是到了家门口又不想看朋友,想打道回府了就会打道回府。“乘兴而行,兴尽而返”见不见得到现在无所谓,重要的是保持一个“兴致所至”的过程,这是最重要的。
三、魏晋风度的中国文化史意义
从中国文化史发展角度看,魏晋风度是中国古代士人文化替换帝王文化主角地位的重要转换枢纽。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转向具有划时代意义。
过去我们学界在谈到传统文化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用两种文化来形容概括我们的社会文化属性。哪两种?有的人把它形容为雅文化、俗文化。雅俗文化,这是一种区分。还有一种区分,国外的一些学者把它叫做大传统和小传统,这也是一种分法,大小传统其实表述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一种高雅形态的文化和一种比较接地气的文化。
我经过研究思考之后,我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除了这两种文化之外,其实应该把这两种文化分解开,把中国文化从三个板块上来认知它。这三个板块在我看来,既是一个可以区分的并列关系,同时总体上也是一个纵向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个情况是什么?我把中国文化分成三个时段,叫做中国文化的“三段说”。
第一个时段叫帝王文化。帝王文化大致是什么时期?夏商周三代一直到秦汉这一段,我把它叫做中国文化形成的奠基时期,叫做帝王文化,它大概有2300多年时间。
这个时段中国文化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帝王搭建活动舞台。从诸子百家的思想到各个方面:政治体制、官僚体制、祭祀制度、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等等,特别是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大家都知道诸子百家这个时代是我们中国思想文化最丰硕的时候,但是我有一句话要说,你纵观一下诸子百家思想,可以说所有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可以归结到一点:他们都在为当时的帝王请做说客。儒家说你要靠仁政去治理国家,老庄说你要无为而治,其他所有的诸子百家归根到底都是给帝王提供治国方略,尤其是文学艺术的方面,我们当时的各种史书也好、散文也好,诗歌也好都是帝王文化,比如能够代表当时文学风貌的汉大赋,简单来说,它就是在给帝王的宫廷园囿等等场面做渲染、造声势。所以,整个先秦两汉就是帝王文化的背景。
第二个时段,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唐宋时段,我把这一段中国历史文化形容为士人文化的时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时代。这个时段很重要。我之所以要提出中国文化三分说,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对士人文化要有足够的新的认识。因为从魏晋开始,整个中国文化掀开了新的一页。过去都是在给帝王造声势,而从魏晋开始,舞台的主调变了。从给帝王造声势变为给文化的知识分子自己来搭建舞台,给士人自己搭建舞台,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从社会政治到知识分子个人。这个时期包括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这前后大概有100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说中国文化整个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当然从大背景上来说,帝王文化它的根基、它的稳固还存在,但是以文人学士为主体的中国士人文化,开始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一个主打系。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我们中国文化才真正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局面,从王羲之书法、顾恺之绘画,再一直到我们大家熟悉的盛唐诗歌、唐代散文、宋词等等,这些都是知识分子文化的精华代表。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化的时代,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唐宋,这是士人文化的时段。那么作为士人文化这一段,大致背景是怎么样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崛起是士人文化形成的一个社会基础。从唐代开始的科举制度是文化得以延续的社会保障。士人文化的主要成就和特征这么几点:
第一,在结束了百家争鸣和独尊儒术的阶段之后,取得独立人格的士人精英们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以往的思想文化来进行解读和整合,整合这个字很关键,什么叫整合?过去诸子百家时代,儒、道大家各谈各的。而从魏晋玄学开始再到唐宋新儒家的出现,说到底就是试图把之前的很多思想整合在一起,以玄学为代表,使当时的思想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士人色彩,这在魏晋时期表现的尤其明显。
第二点,文学从其他的实用性文体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精神文化载体。这个我要简单解释一下,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文学可以说已经有了,但它不是一个很纯粹的时段,所以我们今天要读中国文学史的话,你看一看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文种比较混杂,《论语》、诸子的文章,这是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左传》、《史记》也是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尚书》也是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当然还有《诗经》和《楚辞》了,这些东西都是混在一块儿的,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界限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刀切开,明确了呢——就是从魏晋。一刀切开的好处就是文学就是文学,实用性的应用文写作,比如报告、申请就区分开了。文学要从那些实用性的、应用性的写作当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东西。这个独立的东西后来发达了,从赋发展到六朝时期非常繁荣的一种文体——骈文。骈文在文学史上曾经有一段名声不太好,因为大家觉得骈文太深奥太复杂了,很多人读不懂,唐代的古文运动开始扭转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骈文的话,可以有另外一种评价。正是骈文的出现,才告诉人们什么叫纯文学,骈文才是纯文学。所以尽管有大家对骈文、对赋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你要翻一翻古代文人的文集、别集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很统一的规律和现象,是什么呢?所有的古代文人没有一个人不认为骈文、赋才是真正展示他们文学才华的天地和场所。所以,所有的文集排列顺序都是怎么排列的?骈文和赋都是在第一位的。因为他认为这是最能代表我的文学才能的地方,后面也可以有应用文等等,但是文学的东西是第一位的。这就是所谓的文学的独立性。过去鲁迅说魏晋实现了文学的自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文学从实用性的东西分离出来,文学只有独立了,才能可能朝着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得更加繁荣。
第三,体现文人志趣情怀的各种文学样式得到全面的发展。它们既是文人个人修身养性的手段,也是整个社会普遍热衷的陶冶性情的途径,并且也构成了整个社会文化千姿百态、繁花似锦的灿烂景象。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提到文人士大夫的修养,有一种说法叫做“琴棋书画”。我查了一下,琴棋书画这个说法在唐代正式形成和使用。实际上这四种修养分别已经从魏晋时期,慢慢的从社会实用性方面转到纯粹性方面来。围棋、古琴、书法、绘画,当然还有更多的是文学。
第三时段,我把它叫做中国文化的市民文化时段,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变异时期,这个时段从宋代已经出现了萌芽,它正式的表现是在元明清这三个时代,可以说元明清是中国俗文化、市民文化主体的时代。这个时代随着我们城市经济的繁荣,不仅产生了数字庞大的市民阶层,同时也直接刺激了广大市民阶层精神文化的需求,而这个精神文化的需求直接导致了我们宋代以后市民文化的繁荣。市民化其实不光指文学,其实也包括思想、宗教……都是从高大殿堂走向普通老百姓的,使得市民化形成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色块,市民化主要的特色和精神表现的是这样的:
首先是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文化氛围的形成。
第二是出现了多种以市民阶层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各种文化样式,尤其是文学艺术样式,像元杂剧、明清小说(章回小说、话本小说),还有很多讲唱文学、地方戏等等,这些都是市民文化文学样式的表现。
第三,从意识形态到各种艺术形式,普遍出现了为市民阶层的利益全力呐喊的呼声,这是明代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李贽的思想根源于王阳明,李贽吸收了王学左派一支的思想,之后进行发扬、变异,出现了为市民文化张目的文化思想。
我前面说了关于魏晋历史过程的描述,也说了我对于中国文化三段论跨分和看法,其实说到底这些都是铺垫。铺垫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铺垫,说明魏晋风度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第二阶段——士人(知识分子)文化时段的开场戏。我们中国文化舞台新的一页展开之后,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由过去的帝王文化的政治舞台转化为人生的文化舞台。所以中国士人文化起始的魏晋时代,其文化蕴涵的核心就是从帝王文化关注国家社会的家国视角,转变为士人关注个人人生价值和真谛的个人视角,这个转变为我们中国文化从社会舞台转向人生舞台,展示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文化张力和前景。
通常我们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多少有一些了解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唐代文化甚至盛唐文化,这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鼎盛时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在赞美、向往盛唐文化这一中国文化鼎盛时代的时候,人们往往容易忽略了一个东西:如果说盛唐文化是一个灿烂的、丰硕的文化果实的话,我们大家考虑过没有?如此灿烂、如此丰硕的文化果实需不需要有一种滋养它的阳光、土壤、水分、营养呢?答案显然应该是肯定的,从逻辑上看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滋养盛唐文化硕果的阳光、土壤、水分、营养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这里讲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把士人从汉代帝王的管束当中解脱出来。汉武帝身边有一些文人,像司马相如、东方朔。东方朔曾用一句话形容他在汉武帝身边的生活感受是“伴君如伴虎”:这就是汉代的知识分子和帝王的关系,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是,魏晋时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当时的门阀士族阶层),这个阶层首先在经济上完成了自己的独立,完成了经济上的独立之后,他还要在政治上寻求自己的一些地位和权利,在完成了经济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权力之后,他们要做一台更大的,上演一出更大的戏——文化大戏。也就是说当它解决了知识分子个人的人格独立问题之后,才使得中国文学的独立有了实现的可能;知识分子人格都没独立,有什么文学独立?所以我们很多人,大家在看到盛唐的文化灿烂果实,往往容易忽略这个方面。因此,魏晋风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好好去了解,并努力寻找其中某些现实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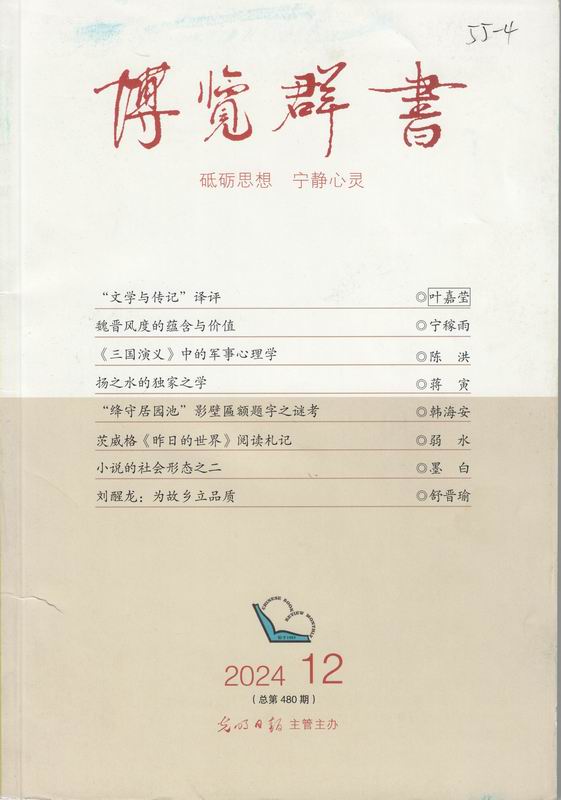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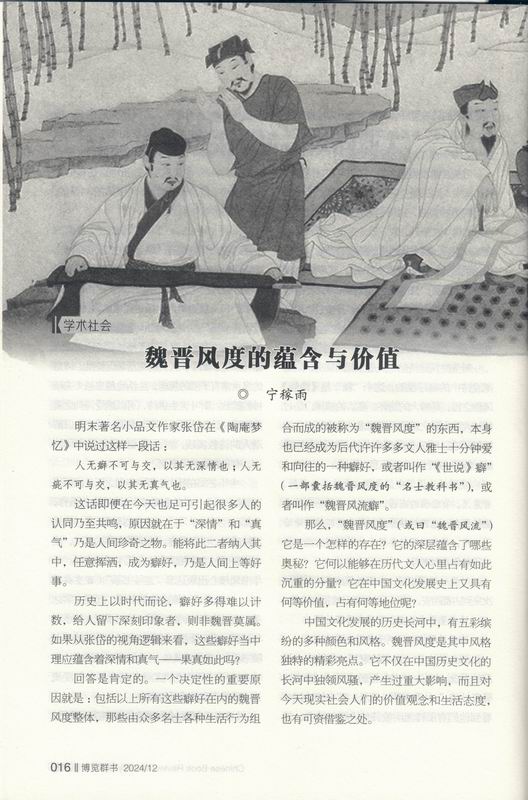
(本文原载《博览群书》2024年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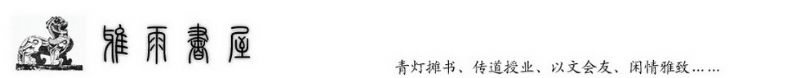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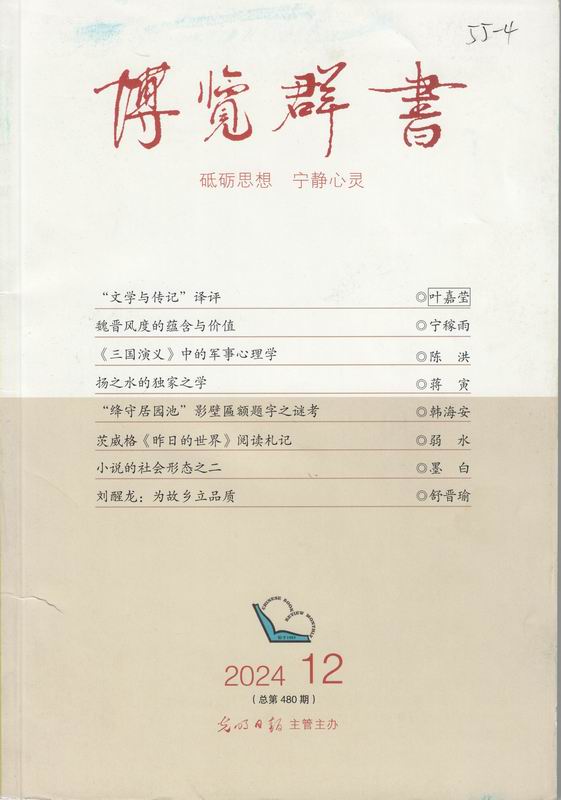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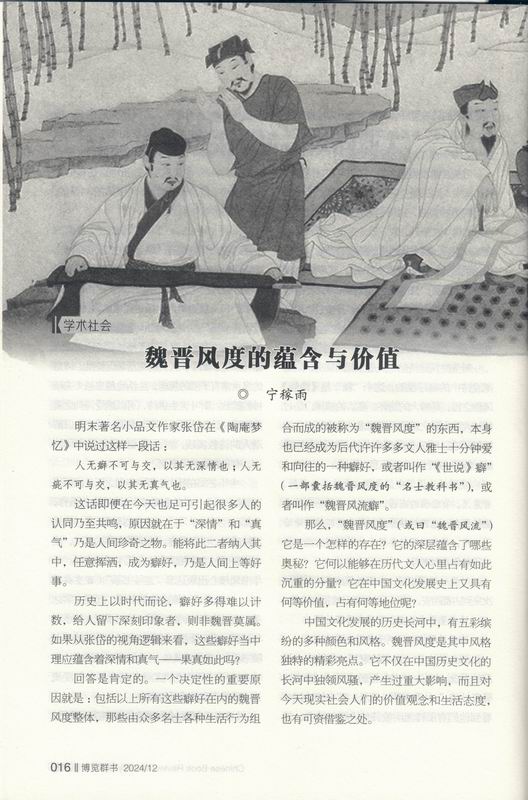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最新评论